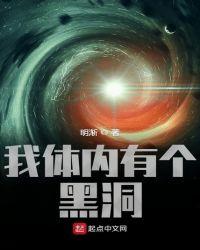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焚心劫 歌词 > 第43章(第1页)
第43章(第1页)
怀里人温驯极了,自己给他穿衣服系带子,毫无反抗,乖乖靠在怀里,大概烧糊涂了,偶尔还在自己肩头蹭几下。南玖低下头,用下巴贴了贴他的额头,那人闭着眼睛,微微睁开一条缝,糊里糊涂地笑了一下,毫无心机也似,南玖知道,这是真烧糊涂了。
床铺是湿的,没法躺,自己总抱着他,他也不舒服,南玖扬声叫:“王宝!”
王宝过了不过一眨眼的时间,就应了声“在”,南玖叫他进来,他便弓着腰小跑着进来。南玖知道他是机灵人,只道:“叫太医来,顺便把这床铺重新铺一遍,软些。”
王宝领了差事,小跑着走了。怀中人动了动,稍稍仰起头,有气无力地勾着嘴角道:“我以为刚刚是做梦呢。”
声音还是哑着,南玖听着一阵阵心疼,搂的更紧了些:“怎么病了?我不叫你给纪清言送行,跟我置气么?”
“不是……”他轻轻咳了两声,“我给清言写了个册子,上面记着如何治水,时间来不及了,就熬夜了。”
“你还懂治水了?”南玖哭笑不得。
“我不懂,年仁方懂。”花清浅蜷的更紧了些,打着哆嗦,“当年他上陈治水的折子,大多我都看过,一条一条,还在眼前。我在沛河边上长大,所以不需要亲见,就能想出该是何种情景,清言什么都不会,不若,我帮个忙。”
“不会,摸索着就会了,你帮忙,却把自己忙病了。”南玖虽然责怪,却带着些宠溺。
“哪里有时间给他摸索,陛下,那都是你的百姓。”花清浅的声音沉下去,这世间除了南玖,不会有第二个人听得出其中的痛悔,“况且,我自己任性,一定要杀年仁方,如今的后果,也该我承担。年仁方是我朝治水的第一人,没了他,要有多少百姓遭灾,我这条命,只怕都不够赔。”
“清浅,没人知道,这是朕和你的秘密。”南玖低头,吻在花清浅的左眼,依旧是滚烫的温度。
清浅笑了笑,顺从地闭上了眼睛:“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够我遭报应的了。”
作者有话要说:此章完成。
南玖说,我是皇帝,富有天下,我爱清浅,我要给他最好的!
清言说,我一介书生,为复仇而来,也能步步为营,掀起滔天巨浪。
邱含墨说,我出场不多,着墨不多,隐藏最深,你们谁能知道我要做什么?
三个小攻各有千秋,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呢?
王宝很快就带了太医进来,南玖守在床边,见来的是太医院医正黄明奇,知道他医术了得,稍稍放下心。花清浅一阵清醒一阵糊涂,浑身冷得发抖,感觉到有人抓自己手腕,往回缩了一下,睁开眼睛。
早就有下人来换过被褥,福伯见着花清浅的样子,更是难过的差点老泪纵横。如今花清浅深陷在被褥里,本就白净的脸更如纸一般,几乎透明了。南玖一边用布巾沾着水润湿花清浅的嘴唇,一边轻声吩咐:“仔细瞧,有什么好药都用上,不妨事。”
黄明奇今年六十有七,太医院里大半辈子,见过的稀奇事多了,与面前这位被子里的人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何尝见皇帝这般低三下四伺候过人。听着皇上的话,小小的高热,竟然洪水猛兽一般,莫不是,已用情至深?
他这边厢想着,那边厢把脉,脉象知道了,又去翻花清浅的眼皮。花清浅挣动了几下,很是不情愿,一劲躲着,南玖上前按住他的肩,轻声哄道:“叫太医看看,开个方子,吃了药就不难受了。清浅,听话。”
花清浅的手摸索着,像是要抓住什么,南玖立刻握住他手,他安静下来,黄明奇趁这机会立刻翻他眼皮。一番诊视下来,行了个礼,便去外间开方子。王宝跟着出去,黄明奇甫出门便问:“万岁爷这是……”
王宝把食指放在唇上,“嘘”道:“黄太医只管瞧病,别的都别管了。”
“那我这方子……”
“黄太医是明白人,开便是,花大人这病早一日好,黄太医早一日领赏。”
黄明奇安下心来,心中暗叹一声“祸水”,手握毛笔,却是斟酌再三才敢下笔。
内间里,花清浅用了好大力气将眼睛张开一线,南玖立刻凑上去,抚着他的脸问:“怎么了?哪难过?”
“你……离我远些,仔细……仔细过了病到你身上。”花清浅每说一个字,嗓子都着火般疼。
南玖皱着眉,无奈地笑,这个人怎么病了还是这般?他拉了拉被子,柔声道:“朕是真龙天子,不会生病的。”
花清浅笑起来,眉目间堆砌着疲惫:“瞎说,这些我从来不信。你帮我叫福伯来吧,连累你生病,我会被折子淹死。”
“别人照顾你,我不放心。”
“我的陛下,你此生,可曾伺候过人不曾?”
南玖瘪着嘴,不知道忽然跟谁置气。花清浅笑了笑,疲惫地闭上眼睛:“帮我叫福伯来,你在旁边看着还不行?”
这才同意,扬声叫福伯进来。福伯眼睛红红的,几乎扑在花清浅床边,替花清浅敷上冰袋,又拿热水擦了手脚。花清浅开始还偶尔眯着眼睛看看周围,后来睡沉了,什么也不管,任福伯动作。南玖看着福伯轻车熟路的样子,又想起刚刚太医碰他一下,他尚且挣动,这才知道,花清浅心里头那本帐算的多清。只怕这世间人早在他心里标了名,谁是能信的,谁是不能信的,谁是敬而远之的,谁是不能得罪的,他心里头都清清楚楚。
那自己在他心里,叫个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