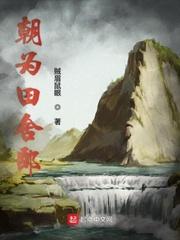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春庭寂格格党 > 第9章(第1页)
第9章(第1页)
那是受死罪的意思,看来此刻匍匐在我马前的人正是滓乌那个没能逃走的皇子。
忌刚走在马前,右手按着身侧的佩刀,高声道:“大将军在此,何人受降?”
那人更是俯低身子叩首,洁白高贵的额头已抵着地上的黄土,“罪臣宁雅叩见大将军,请将军赐臣一死。”
声音如同流泉一般流畅温润,他说话时舌头微微带着卷,别有一番风味。
“你有何罪要本将军惩处,不妨说来听听。”
“遵命,”他略微抬起脸来,手指撑住身体,已极卑微的姿态继续说道:“罪臣一家不忠不孝,不念怀天子恩德,反而狼子野心恩将仇报,死有余辜,虽蒙将军恩赦许降,但罪臣也委
实无颜再苟活世上,请将军即刻赐死,以平天子之怒。”
我沉吟了一会儿,这个叫宁雅的皇子看上去弱不禁风,可说出来的话却十分厉害。
虽然他跪在我面前,自称罪臣,但他刚才的话,尤其是最后一句,说赐死他是为了平天子之怒,这就证明他有不服之意。
明明是想要谋反的死罪,怎么就成了为了平天子之怒而杀他呢。
真是有意思。
我眯起眼睛,锐利地打量着他良久,忽然笑道:“天子仁德,不愿轻启战端,不愿百姓受苦,你父子今日这般作为,实已犯下大不赦之罪,但天子宽厚,愿赦死罪,然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望你能诚心弥补这一身的罪愆才好。”
他面不改色,身姿流畅的再度拜倒,“多谢天子不杀之恩,天子仁慈,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留下两名副手继续追杀滓乌国君和处理一些善后事宜,自己则带着大军班师回朝。
这一仗,整整打了五年多,消耗兵力财力不计其数,还让我和熙茗这么长时间都没能再见,但对帝国来说,却是大功一件。
它彻底的平息了叛乱,也打击了那些蠢蠢欲动的分据一方的诸侯们,这样皇帝至少可以在国家安全方面松一口气了。
马车悠悠地前行着,我半靠着车壁,胸口传来一阵阵尖锐的刺痛,让我几乎无法呼吸。
赶的太急,太想要早点解决战事,回到京城,回到熙茗身边。
但右胸的箭伤却不答应,在攻破皇城的当天,就极为凶猛的再度发作。
创口迸裂,比之前刚受伤时更为厉害。
我收下了宁雅后,还没来的及安置当夜便起高热,人事不醒伤口血流不止,几乎把忌刚吓死。
这已经是第七天了,我没让他外传,为了消除主帅伤重的不利消息,和防止有人乘机蠢蠢欲动,昨天我还特意上马,出去转了一圈,但结果就是,今天整整躺了一天,还是提不起力气。
以宁雅的心思智慧,我担心弄出什么事情,毕竟此地离滓乌耶不算太远。
因此清醒过来的第二件事就是把他放在身边。
不过他这次倒更是让我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