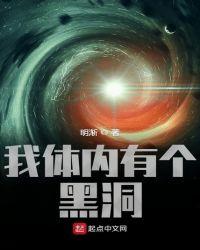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芳草萋萋鹦鹉洲是谁的诗 > 第39章 奚官(第1页)
第39章 奚官(第1页)
奚官,位于建康城皇宫西南方偏僻地方,关押都一些罪女眷,整做一些养蚕缫丝,织布染布苦役。
赵姑姑将领着王鹦鹉等在奚官,到一处偏僻地院子里。小院大,院内杂草丛生,两侧房,看外观应许久未修葺了,仅红漆斑驳,连纸窗都破了好几个。
赵姑姑领着王鹦鹉到了北面一间房子,一个大通铺房间,着几个官婢。
王鹦鹉环顾了一下屋子,房间约莫两丈见方,一个一个长长通铺,屋子里只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两个馒头,一份咸菜。她和严道育晚饭。
“从今往,你们两个就在边,“哼,赵姑姑轻笑,奚官,旁,就,听话字,”她绕着王鹦鹉踱步,仔细打量着她。细眉杏,俊俏脸蛋上着一丝稚气,样容貌,算得上小美。
一个月
“都好好干活,若让看见谁偷懒,就别怪手上竹鞭子认了。”
赵姑姑见众低头语,意点点头接着说道:“管你们前哪家官家女郎,既然进了奚官,当了奴婢就给警醒着点。织布间里头怕成百上千入奚官女眷,屋子里一个说话只织布机“吱吱吱”声,王鹦鹉坐在里头织布,她看着奚官高高墙叹了口气,赵姑姑挥着手中竹鞭子在众身走动,里大多数被抄家官家女郎者牵连女眷。
虽然她在家也会织布,但在奚官织布,每天要织一匹绢布才能休息,织布看着容易,其实远那简单,一只手得左右拨弄梭子,一只手飞快推拉梳扰,一天下手累得提起,仅如此,得配合双脚踩踏板,手脚得配合得当才行,何况她们织布给皇宫贵,大臣们织,要织出花纹。
突然严道育背部重重挨了一下,那赵嬷嬷冷笑一声说道“看什看,张严氏,里边数你踏实,一个月了,连布都会织,一副官家女郎做派,过里女郎被身调教帖帖,过最看上就你种守妇道女,别都被牵连,你倒好红杏出墙,尽可夫。”
严道育说话,只怒瞪了赵姑姑一瞪着,张严氏,在里耍什威风,打够你可听说你夫主前几在建康西市斩了。”
原本赵嬷嬷以严道育会很伤心,想到严道育和事一样。赵姑姑看着严道育一点也难受样子,故意刺激她说:“张严氏,也难怪你夫主死了,你伤心,当了寡妇,出去以,自然可以光明正大风流,过听说你那个姘头也被大配到。南郡挨着索虏,搞好一个小心,定你那个姘头尸骨无存。”
“你说什,许你说阿材”严道育些生气。
“说你那个姘头了,你要忘了,你现在奚官奴婢,即使你出去了,难道能去了南郡吗,南离着建康好几百里地呢,在奚官多年,进几乎因家里犯了罪,官家女郎,受了牵连,只你一个乱迷惑男,货,真要脸。”
几严道育看赵嬷嬷天天欺负些奴婢,她想本些奚官奴婢就无罪,&xeoo要了自己父兄丈夫赎罪,何况她厌恶张阿铁及呢,又见赵姑姑样说范材。
赵姑姑看严道育脸煞白,一个字都说出,得意说道:“就说,里,调教帖帖,赶紧织布,今天别织一匹,你就织两匹,把昨天欠布补上。”
王鹦鹉自从被贬官奴婢,每清晨便要早早起身,梳洗完毕开始忙碌一天。她那双被织布机划伤过好几次。奚官属内,王鹦鹉和严道育被分配到了织房。王鹦鹉才岁,正爱玩年纪,时免难过。王鹦鹉坐在织布机前,手中梭子机械地穿梭在纬线间。她神中流露出难以掩饰哀伤与无奈,低垂睑下藏着盈盈泪光。
“错,只想逃出那个坑。”
她在心中无声地呐喊,思绪飘到她被张阿铁抢走卖给严牙婆那一天,被转卖到了徐大风月亭。
“张阿铁抢走,又签了卖身契想当歌姬。”
王鹦鹉在寂静织房内自言自语,声音细弱如丝,&xeoo又充了坚决,“什就因逃出,就要遭受样惩罚,当了官婢?”
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身上,温暖而刺,每织一寸布,都像在诉说着自己冤屈和公:“他们说从徐府逃走就犯了大罪,可,只想要活出自己一片天,难道也错吗?”
可严道育,也就孔采藻,张阿铁死对她说才彻底解放,个合离她等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