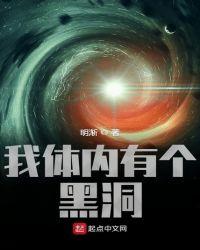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和秦始皇合作入侵异世界免费 > 第40章(第1页)
第40章(第1页)
赵政在那里久久驻留,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坐在案台上,打开一卷案上的竹简,却发现了里面夹着的一封信,墨迹早就已经干透:
殿下,我是子方,在大秦将近三年,受恩于您,万分感念,但是我要离开了。就像您可能猜测过的,我来自遥远的地方,也算是所谓的世外之地,所以我看上去也和这里的人有些差异。大秦地广物博,国君善治,若我为大秦子民,也会心甘情愿为之驱驰。希望我的离开不会造成什么影响,还请您代我向卫厘告别。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曾答应您的果脯,或许也无法应诺,现将制作方法书于此处,聊以补救——
话未尽而断,应是还没写完,子方一向很少出错,这帛书上却遍布涂抹之迹,可见十分纠结。
这封离别信简短到有些无情。
子方早就知道自己会离开,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赵政攥着帛书,反复看着,想要从那一笔一画中看出更多东西,但什么都没有了。子方到最后也不肯告诉他实情,影影绰绰地遮掩,不知道从那里来,也不知道到哪里去。
可终究斯人已逝。
夜凉如水,年轻的秦王仍在章台宫伏案不倦,没有一个宫人敢上前惊扰。
赵政继位以来,夜以继日、焚膏继晷更胜先王,虽然年少,且大政在国相手中,他也未曾怠惰。再过几年行过加冠礼,作为秦王当政柄权就再也无人能够置喙。
“大王,姚贾大人刚从齐国返回,请求面见大王。”
“让他进来。”
“是。”
姚贾风尘仆仆赶来,一到咸阳就让人去报告大王,连洗漱打扮都没来得及,灰头土脸的,差点儿被侍卫拦在外面。
“臣姚贾参见大王。”
“姚卿坐吧,何事如此急切,信上不是说过两天才能回咸阳吗?”
“谢大王,臣深夜面见,确有要事。臣出访齐国,拉拢齐国相邦后胜,那后胜贪财好色,仗着是齐王的舅舅当上了国相,得到几回臣送上的金钱美玉,就答应了要劝阻齐王与其他五国合盟攻秦,还要派使者出访我大秦。本来相谈甚欢,突然冒出来个账房先生,说我们给的数目有问题,之前从未出过这样的事……”
“这后胜贪财,倒还知道斤斤计较,姚卿无需为大秦省下那些钱,都给他就是,反正日后还要让齐国都吐出来。”
“大王啊,臣要说的不是这个,”姚贾倒是不拘小节,不顾形象地抹了把脸上的汗,继续道:“臣还疑惑这后胜怎么突然变精明了,看那账房先生,突然想起来您让找的那个小先生,臣之前没见过这个先生,后来看过画像才更确认了——”
“你说什么?”
赵政本来还一边看着竹简,这下直接扔下了竹简走下案台,眼中充满不可置信。
四年了,这样的消息不是没有过,但每次都是无疾而终,赵政甚至想过干脆放弃继续找,反正子方也不一定想再见他……可是子方离开的时候身受重伤,自己总要确认他的安全吧……赵政如是想。
姚贾还从没见过大王情绪如此外露,也赶忙站起来走到秦王身边,“大王莫急,臣知道您一直在找此人,后来又特地去打听了一番,不过他好像也是不久才出现在后胜府中,府里的人也不大清楚,不过臣仔细对照过,的确是画像上那个人没错。”
“继续说。”
“臣赶着回来见您,也是怕信上说不清楚,那个账房先生啊,我想想,大概跟您差不多高,”姚贾大逆不道地拿手笔画,又心虚地缩回去:“倒是能说会道,有股说客劲儿,而且长得齐齐整整,不像给人当账房的,倒像是哪国流落的公子呢。而且算账算得清清楚楚,臣也只能推说是自己没弄明白,哎呦喂,大王,后胜不知道吞了咱们多少钱……”
姚贾还在心疼钱,赵政冷冷睨了他一眼才住嘴,继续道:“臣急着回来,咱们在临淄还有不少密使,臣已经派人紧盯着他啦,您不用担心,一有新消息就会来报的。对了大王,那个小先生以前在秦国当官吗?看年纪这么小不像啊。”
赵政斟酌了一会,开口道:“这你就不用管了,只要知道他平安即可,也不要贸然惊动他,多派些人手看着。”
“臣知道了。”
“另外,你多久赶回来的?”
“齐国千里之遥,臣累坏了好几匹马,也月余才赶回来,不过臣甘心为大秦肝脑涂地,感谢大王挂怀……”
赵政若有所思,齐国确实太远了,他脑海中突然划过一个荒谬而大胆的想法——说不定现在朝政掌握着吕不韦手上也是件好事,秦王拍了拍姚贾的肩膀,温声道:“姚卿为大秦千里驱驰,居功至伟,此番受累了,不过寡人还有件事要你去做……”
临淄城
一年前,临淄城外。
子方刚醒来,就发现自己躺在简陋而颠簸的马车上——不,这简直不能称为马车,只是一匹马拉着的木箱,身下都是草屑,像是运送粮草所用。子方头痛不已,像是脑袋被车轮反复压过去,身上也好不到哪去,他勉强坐起身来,揉了揉眉心。
自己身上穿着沾满血渍的护甲,心口疼得不行,身体也仿佛不是自己的,更糟糕的是,他什么都想不起来——眼前是不断变换的风景,似乎是在郊外,荒草丛生,没什么人烟,前面还有一队马车。子方头疼得想撞墙,根本无法思考,干脆继续闭上眼躺下来。
许久,赶车人终于停下来,子方缓过神,再次睁开眼睛时,却对上另外一双眼睛,子方吓了一跳,却又被泼了一脸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