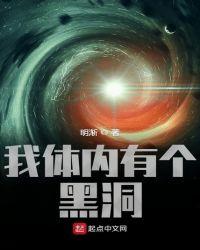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春花与玉去哪看结局 > 第92章(第1页)
第92章(第1页)
眼里的光烧得愈发灼热了。他折死了千万只蝴蝶,终于要迎来他最爱的一只。作者有话要说:连我都有点恍惚了,变态大哥最爱的到底是小椿还是霍钰……生疏窗棂上落了只金蝴蝶,金得昏黄,而且静谧,让闻人椿想起文在津屋中常年燃着的佛香。他是佛门好弟子,照顾家中生意的同时,从不忘早课、晚课。闻人椿问过他:“一日不漏地念经礼佛,真能保佑平安顺遂吗?”“若是真心向佛,则不该求回报。”他双手合十,目不转睛,又同闻人椿讲了古时释迦牟尼佛割肉喂鹰、舍身喂虎的传说。那故事感人,为天地生物竟要献出自己。闻人椿惊叹之余别无它想。毕竟她如今爱意正浓,不得点化。她原本心想,如若念经礼佛能得平安,那她也要买个佛龛日日钻营。既然不能,那便算了,她还有俗世无数事务要料理。心不诚,大抵真的要遭报应的。听闻霍钰入狱,是在文府。文在津见她的第二句便说了实话。他没有要瞒她,霍钰也没有。因为他们都没料到闻人椿会亲自回到临安城。文在津要她无需担心,只言片语说得并不多。闻人椿倒是听懂七八分,知道霍钰这招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可许大人那只狼,套着了会不会咬伤他自己呢?还有更重要的,许还琼是许大人的女儿啊。她与霍钰是否要因此重逢,又要生出怎样的故事。于是那颗心就似是被人穿针引线吊了起来,时不常地往上拎一拎,连睡眠时都不得轻松。约莫过了半月,离除夕夜还有三日的时候,霍钰终于出狱了。临安城有眼力见的都瞧得出来,那是许大人专用的双头马车,马头耳侧套了红穗穗一般的银饰,辅以一般人家连见都没见过的虎毛皮。宝马要什么虎皮御寒,霍钰从窗中望过去,只觉得热闹而可笑。不止宝马,包括他自己。他的身上不也套着一只名为许大人亲侄儿的壳嘛。这个在娘亲生死关头撤得最快最干净的人,却是他此刻不得不攀附的贵人。他笑,看不出喜悦满足,也看不出讽刺怨怼,倒是适合拿来与许家父子演推杯换盏、交浅言深的戏码。敞亮厅堂中,珍稀家宴前,没人提起二娘,也没人提起许还琼。他们舅甥兄弟好似感情亲密无间。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灵性的。霍钰只在许府耽搁了两日。不过短短时日,他这位舅舅也算给出了诚意,将两个亲儿子的弊端暴露无遗。一个无才,只知拾人牙慧,一个无德,只会向外泼钱。故而他将头脑堪用的亲侄子招入门下,并非心血来潮。然,只是悉心培养、无私付出,又怎么会是他的舅舅呢。霍钰摸着手上一串与许家父子一模一样的檀香珠,又重新计较起来。彼时,闻人椿正在文在津的药房里折腾草药。外头风雪淅淅沥沥,她却忙得热火朝天。她骨子里是个爱做活的,与其躺在房中悲春伤秋冻个半死,不如给自己一点事做,身子和心都能暖和起来。不过她手头这项活有倒买倒卖的嫌疑,先是将此处的方子传去系岛,再将系岛的方子复原给文在津。不晓得系岛的野方子能不能在这儿赚上一票。也不知道这一票能帮上霍钰多少。药草磨成暗绿色汁液,她将其封存后便撑着脑袋在木头长桌前发起呆,浑然不觉门外正有人对着她发呆。雪从树梢滴落化成水。霍钰摸了摸鼻子:“她何时来的?”“有些日子了。我说你自有筹划,她也没多问,就一直乖乖在这儿候着。”“哪里乖了。”只消看着她,霍钰便忍不住带出笑意,纵使理智告诉他,她不该来的。文在津几乎不可闻地叹了口气。“方才是许府的马车吧。”“是啊。”“如今收手还来得及。”“你知道不可能的。”“我说的是她。”不等霍钰接话,屋内人的眼角余光已经看到了他们。她就知道右眼跳、好事到,这不霍钰回来了吗?闻人椿顾不得文在津在场,也忘了霍钰的腿疾受不得重力,起身的时候甚至还差些将椅子绊倒。“霍钰!”她连走带跳地扑了过去,今日的雪都下得没她欢快。于是霍钰低低回了文在津一句:“你太悲观了。”便大步迈开,将眼前这个乐不可支的女人收到了怀里。他也想她了。只有她,才能让他片刻忘记苦难、罪恶的枷锁。“有情人饮水饱,从此苦难不煎熬。”途经花园,台上人的唱词脆而洪亮,这是文夫人请来的时下最红的戏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