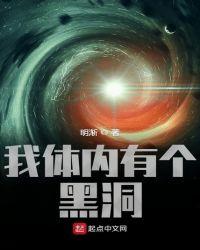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十二歌词 > 琉璃梦之二十三 故事(第1页)
琉璃梦之二十三 故事(第1页)
白日游街、暮夜听书,较之从前压抑难耐的宫中日夜而言,相当惬意了。
但柔安偶尔还是会想起数月前深宫中的挣扎求生,错觉近日的适意是梦幻泡影,一个一戳即破的梦。
但她只容许自己恍惚片刻,总是很快惊醒,拼命回忆现实的微薄的快乐,拼命回想那些莫名出现的但让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肆意的模糊记忆,挣扎着不被绝望吞没。
幸而,她在崩溃之前走出了头悬利刃的宫掖。
天不绝她,在她命悬一线时,靳玉出现了。
天予不取,必受其咎。
哪怕只有一点让自己变得强大的机会,她都会牢牢抓住,不论是进入虎狼环伺的域外荒原,还是破出牢笼浸身江湖,她都会尽力摆脱任人鱼肉的境地。
靳玉未必不曾察觉她的执念。
每当她问及江湖旧事,问及门派来历和各家武技臧否,靳玉一改寡言,皆为她细细道来。
一日,靳玉讲罢江湖大势,见她如有所思,问她,可知初入江湖当以何为重。
她沉吟片刻,试探答道:“当有自知之明?”
“自知之明重要不假,可新涉江湖,对他人无知,又如何自知;便有所知,又有多明呢?”
“那我便不知了…恳请赐教。”
“初入江湖,江湖波诡云谲,百事之先,当是慎择一引路之人了。”
柔安一脸恍然:“确是如此。我若是新人,必要多多瞻仰才高德劭的前辈的风姿,以求以人为鉴,以求见贤思齐,只是,我有心结交,却要如何得遇可靠前辈呢?”
靳玉看了她一眼,牵出一抹笑:“你有心,机缘自不误你。”
柔安执壶,斟满茶盏,捧到他眼前。
“我自然是有心的。”
“你要一直有心才好。”
靳玉饮了茶,转而为她普及人体筋穴脉络,又讲解一些健体防身的法门。
柔安求知若渴,一一练起不提。
她沉心学海,不问窗外事,她的侍女却不能都如她般镇定。
木蓉见公主近来总不要她们近身侍候,一人独守内室,只道她背井离乡,忧思甚多,捧了州牧公子奉上的宝货奇物,劝她应其所请,外出览胜寻芳才好。
木莲倒没有木蓉那样焦虑,只更多打听来此地趣闻,说与公主解闷。
木蓉三番四次催她一同想法开解公主,被撺掇得急了,反过来说了木蓉几句——
“人道你比我规矩,在宫里我也事事以你为先,怎么你出了宫倒糊涂起来。你从前会做事,要我的强,指使我做事便罢了,如今随公主出降,越发本事,开始要公主的强,做公主的主了。公主当要如何,哪容你我置喙。我看公主这样很好,显见想通了,不像从前任由皇后做主,如今自己也有主意了。我们要去那不得回的地方,公主自己愿意做主再好不过。你离了那个牢笼,心就野了,连公主的话都不听了,闷头乱扑腾。”
木莲想,送嫁队伍行至璃州,蛮地在望,公主多看多想,总好过自暴自弃,她也派不上大用场,无非在公主有兴致时陪伴取乐,在公主没兴致时静守己身,平日里侍候起卧,遇险时舍命相护,就算做好本分之事了。
木蓉被木莲迎头一棒敲醒了一些,但还是心不能定,她也没有狂妄倒自认智谋强于公主,只好更加仔细公主的衣食,回想一路行来尝到的特产点心,收来的名贵面料,以宫廷技艺改制,制出不少新鲜花样进给公主。
柔安无不笑纳,木蓉才松了口气。
柔安将二人言行看在眼里,不是无感于心,却不能据实以告,只不再拒绝州牧公子的提议,多外出逛逛看看,让侍女们也跟着松快一下。
半月过去,柔安按照靳玉所教,每日疲累已极还要强撑仪态,收获颇丰。她一改从前养尊处优养出的孱弱,自觉身体轻盈、动作敏捷了很多。
不过,越练越难,越累越狠,她为了转移注意,也会忍不住向靳玉搭话缓解苦劳,此时心念松懈,难免说出一些平常不会出口的话。
“你幼时习武便是这般入门么?”
靳玉抬手纠正了她不觉偏移的姿势,绕着她一边检查一边道:“不是。这套入门功法虽也是我家藏,但并非我家传绝学,我三岁同父亲学习运气,五岁打磨招式,你年纪已不小,须另辟他径打实基础,我才好传你一些招式应急。至于再多,需待你与我归家,以我家传特制灵药相辅,才能功法大成。”
柔安听明白了他眼下之意,不禁惊讶:“怎么你授我绝学,难道不需令尊首肯?再者,我入门如此之晚,竟还有大成的可能?”
靳玉看时辰到了,正好让她休息片刻。
“我家并无功法不可传于家外的戒律,只是对天赋和品性有些要求罢了。先人恬淡,世辈深居幽谷,外人不得所知也不得其门,故家学不曾外传,如今,缘分既至,传了也就传了。至于能否大成,我家这一功法正是以修炼条件松简见长,习练者功夫到了,自有其所成。”
柔安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