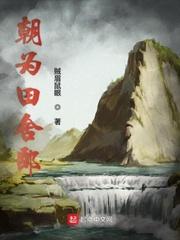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恨春迟忘羡文 > 第四十四章 月恒(第1页)
第四十四章 月恒(第1页)
叶怀昭睁开眼睛,便看见了那双眼睛,温润多情,正无比专注的看着他,瞳孔里印出的只有他一个人的影子,好像心里也只有他一个人。
他心如鼓擂,猛的坐起来,心里慌的无以复加。以至于忘记了手腕上的伤,刚刚撑着床坐了起来,又疼满脸扭曲瘫坐了下去。他心里无比懊恼,怎么在此人面前,总是频频丢丑。
“见过三皇子殿下。”叶怀昭想下床行礼,却被一双手给托住了。
“你就躺着吧,这么让人不省心。”声音磁性温和,语调中带着一丝亲昵。
叶怀昭低着头,“多谢殿下记挂。”
刚刚一番动作,叶怀昭的手腕的伤口又有些撕裂了,一丝淡红浸了出来,给那缠着的白布染上了一丝红色。
一只骨节分明的手,轻轻的将他的左手抬了起来,眉头微微的皱了起来。
叶怀昭低着头,看那修长的手指,一层一层解开缠着他手腕的布巾,露出了里面一寸来长的伤口。“你这伤口,怎么倒像是被咬出来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冰冷。
“那女人是个疯子。”叶怀昭叹了口气说道,反正那人已经死了,不管什么事,只管推到她身上去吧。
“还好你脱险了,你可知,这几日。”余下的言语没有出口,但一丝颤抖的声音还是出卖了他的情绪。
“多谢殿下关心。”叶怀昭微微低头,行了个礼,他没有抬头,只是将目光落在自己被捏着的渗出血丝的手腕上。
“外面有留守的医官。”他想将手腕抽出来。
“哎。”一声长叹在耳边响起,捏着他手腕的力道加重了几分。
那骨节分明的手指,拿起床边小几上的布,沾湿了水,将伤口旁边的血迹擦拭的干干净净,动作轻柔而专注,又用带着薄茧的食指,蘸着褐色的药膏,在那伤口上轻轻的涂抹了一层。
“等药晾干了,我再帮你缠上。”
大周的皇子历来文武皆修,此人的手指、虎口都有一层薄薄的茧,但并不影响手的美观,不像楚青钺那手指,大概是常年握着缰绳和兵器,拇指和食指的关节都粗的有点变形,虎口处的厚茧,掐住脖子的时候,更是摩擦的皮肤生疼。
“多谢殿下。”
头顶响起了一声轻笑声,“你就不会讲点别的吗?”
叶怀昭想了想,两人单独相处,还真不知道讲些什么。
“宜妃娘娘昨日来找了我。”叶怀昭抬起了头,正好和杨景修的眼神碰在了一起,他克制住了自己想要闪避的眼神。
“她大概也听闻里面都是南疆旧物,怕你…”
“你放心吧,我不会再带你下去。”
叶怀昭看着他说:“殿下,里面毒物甚多,机关重重。”
杨景修点了点头,“那宅子是塞鲁班所建,拆不得,但又涉及到是前前朝旧物,怕引起民间无端猜测,只能低调处理,父皇可能会派我处理此事。”他斟酌了一下用词,“此事,你须得守口如瓶。”
叶怀昭点头,毕竟京城脚下有私密的地宫,还是中原罪人所建,史书中的鹤云比那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可歹毒多了。当今天子年轻的时候杀伐决断也算一代守成的明君,但到了中年,却有些超纲独断的苗头。最不喜的便是那朝中御史,但祖上留下的规矩却不得不遵。之前被困在地宫中,叶怀昭就想到,若是此地被发现,陛下定是要私下悄悄处理,绝不让朝中大臣知道,不为别的,就怕他们一道折子接着一道折子的上,为了如何处理鹤云的尸体,引经据典的争吵不许。所以他在昏迷之前,对着章池,干脆隐瞒了第三层,只说看到了鹤云的牌坊和一些毒物。倒不是因为他想迎合皇帝的心思,而是分开的时候,他很快便上了密道,虽然跟那女人缠斗受了伤,但很快便走了出去。但楚青钺黑夜中双目不能视物,估计要等到天明才会行动。万一他这动了什么机关,再将楚青钺困在了七年之后的地宫里,浪费了他的血不说,更对不起北疆的百姓了。
“那里的灯烛里面不知加了什么,会让人昏昏欲睡,甚至丧失神志,还有那毒虫,吸食血肉。我实在是侥幸,所有的衣物都是用一些南疆草药熏制,大概对那些毒虫有所克制。”
杨景修点了点头,“御医们正在赶制驱虫的药物。”他一边说,一边仔细的将那白色的布条缠绕在叶怀昭手腕的伤口上,“下次仔细些,别再伤到了。对了,你握着的那把匕首,华而不实,我下次再为你寻把好的。”
说完站了起来,“说起来,怀昭,你去那地方干嘛?我虽身在宫中,可也知道,子谦他们常去的是长乐坊。”
叶怀昭抬起了头,正准备解释,忽然看到了杨景修狭促的眼神。
“殿下莫要说笑,我只不过看那刘武丢了孩子,带着闪电帮他寻找罢了。“
“怀昭,可有心仪女子?宜妃可是盼着为你说亲呢?”杨景修站了起来,言语温和,眼睛却是一眨不眨的盯着叶怀昭。
叶怀昭坐在床上,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腕,上面仿佛还留着那让人发烫的余温。他轻轻的摇头,“昭还未有成家立业的心思,倒是忘记给殿下贺喜了,听闻殿下的长女已经出世了,算算日子应当要满月了吧。不知可有取好名字。”
“月恒,杨月恒。”
叶怀昭心头大颤,抬头看他,只见眼前之人周身华贵、气度不凡、嘴角含着笑,眼神却充满了挣扎和无奈。
七年前,他们二人十五岁,三殿下杨景修的生辰。叶怀昭送上自己写的字一幅。
“如日升、如月恒,如南山之寿。”
也在那天,圣上为其赐婚,定下了嫡妃。其母婉妃的堂兄之女,三殿下青梅竹马之人,吴绍谦之女吴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