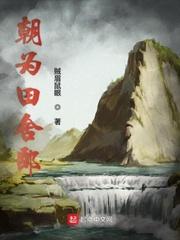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梦见狮子入宅是什么预兆 > 第37章(第1页)
第37章(第1页)
余飞便走过去,只见他在搁鸟食。窗台上落了好几只鸟,扑棱着翅膀在啄食。这些鸟长得胖胖的,羽毛油光水滑,一看就知道在认真过冬。
余飞问:“你养的?”
白翡丽点点头。
余飞心想你就胡诌吧,又问:“那你都认识它们咯?”
白翡丽又点头。
余飞瞅着这几只鸟还都长得不一样,她反正认不出是什么鸟。她手里头滴溜溜转着苹果,偏着头问他:
“哪只是在屋顶上瞅着我们做好事儿的那个?”
他忽的转过头来看着她,默然的,眼睛漆黑幽深。
她顿时笑得花枝招展:“就知道你胡说八道。”
没想到他真的伸出手去,指住了其中一只黑颈灰羽、翅膀和尾巴是灰蓝色的鸟儿:
“这只,灰喜鹊,叫喜田。”
余飞有些傻眼,说:“你怎么知道是它?”
白翡丽双臂搁在窗台上,目光注视着那些啄食的鸟儿,说:
“它的叫声不一样,它叫kwi——kwi——kwi——”
他惟妙惟肖地学着鸟叫,余飞心想还真是和那晚上的叫声一模一样,一时之间竟然分不出他到底是在说真话还是胡扯。但他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又让她忍俊不禁。
然后她就听见白翡丽望着夜色中说:
“它说:亲她,亲她,亲她,我就亲了。”
余飞忽的说不出话来。
☆、摸到他化
他眼尾的样子长得像一枚精致的叶,鼻尖落进群林漠漠的夜色里。鸟儿吃饱了就扑楞着翅膀飞走,这里像一片孤独的圣地。
余飞厚颜无耻地想,白翡丽一个人关在这里太浪费了,就需要她这种人来欣赏。
她转了转手中的苹果,问:“吃吗?”
白翡丽看了她一眼,点点头。
余飞环视一周,白翡丽房中没有水果刀。这苹果虽然被姥姥洗得很干净,她还是习惯削皮吃。她说“等我一下”,就开门下楼。
楼下姥姥姥爷已经出门去了,连虎妞都不见了。
余飞去厨房拿了把小水果刀。她自恃刀功好,边上楼边削,把苹果皮削成长长的一条,又薄又整齐。然而这刀子比她估算的要锋利得多——当她在手里里把苹果切成两半时,力度没能把握精确,刀刃过核如吹毛断发,一下便割进了她的手心里,鲜血涌出。
她受这种小伤受惯了,也没当回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还好没弄脏苹果。
她把苹果挪到右手,左手手心窝起来,免得血流到地上。
她几级楼梯上去,站在白翡丽门口叫他:
“你家的创可贴在哪里呀?”
白翡丽疾步走过来,“你怎么了?”
她毫不吝啬地把左手伸出来给他看:左手掌心到手掌根部静脉处一道血口,手心里已经积了满满的一捧血,想一个小小的血泊,殷红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