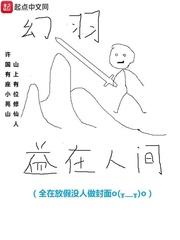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原罪全文免费 > 第69章(第1页)
第69章(第1页)
原来他刚才攀爬而出的土堆并不是这片地上唯一的一个,在这个罕有人烟,却茂密非常的树林里,大大小小无数个突起的黄土堆遍布了树林的这个小而不起眼的角落。那些土堆无声地伫立着,坚守着作为埋藏其中的人的最后归宿的职责。
“咦,你居然没有死?”一个声音在他的身后响起,听声音是个年轻的男人,语调略有些惊讶却带着玩味般的愉悦。
他还没有来得及回头,身后的人已经对他举起了枪口。
当他再一次倒在血泊中的的时候,他把手放在口袋里,紧紧地攥着某样东西。
那东西是扁扁的圆形,带着金属特有的冰冷而坚硬的触感。
——
黑衣的男人依靠在墙角边坐着,低垂着头闭目休息,似乎是睡着了。
李墨白已经一天一夜滴水未进,嗓子眼冒着火,嘴唇干裂地生疼,全身上下提不起力气。但这些身体上的摧残都不如他内心的愤恨来得猛烈,他的怒气似春日的野火般,漫布心头,无处发泄。
他斜睨着身边的莫风,在心里怒骂:可恶的骗子,连累他一起倒霉。
莫风和黑衣人之间究竟有什么恩怨,李墨白并不清楚。之前他们之前的对话,他也是听得莫名其妙。
黑衣人指责莫风杀人,莫风沉默良久,才扯出招牌式的温和笑容:“我想您是弄错人。”
黑衣人回身同空气交流片刻,再转头,眼神无比坚定:“即便我那时不在状态,也绝对不会忘记你的声音。何况……小唯见过你,他说你是,你就一定是,”他的又揪紧几分,冷笑道:“你就认了吧,莫老大!”
李墨白的头上似有无数只乌鸦,黑压压地一片呼啸而过。
还莫老大嘞?这是拍黑帮片吗?到底是哪跟哪啊?!
莫风的眉头锁得更紧,满脸的无奈:“您认错了,我真的不是……”
黑衣人猛地单手掐住莫风的脖子,将他往身后的墙上狠狠地一掼。他从怀里掏出一支注射器,举在莫风的面前,冷冷地嘲讽:“他姓莫,你也姓莫,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不是大毒枭莫老板,你的办公室里怎么会有这个东西?而且我查过你的电脑中经手的账面,每年都有一笔巨大的额外开销用途不明……”他收紧手掌,双目通红,似能喷火:“莫老大不记得我这张脸了吗?我可是您亲手送去地狱的,而且是两次!可惜阎王爷他就是不收留我,所以我活着回来了,回来找你!”
李墨白自见到那注射器并听了关于隐藏账目的事情后,就开始有些信了黑衣人的话,看莫风的眼神不由地肃穆起来。他一直觉得莫风深藏不露,没有想到竟然是贩毒的黑社会大佬。想不到他李墨白有生之年也有机会见一见黑社会的争端。圕馫闁苐可是!这些个恩恩怨怨管他什么事?要看戏也应该捧着个茶杯、打着扇面、磕点瓜子、优哉游哉地远观啊。像他这样被捆绑住置身于戏台之上的观众,是多么地可悲可叹!
要不是他的双手都是被束缚中,李墨白此时也想像夏成一样,45度角仰望天空,林妹妹般忧伤地哀嚎: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
莫风被黑衣人掐住脖子,脸涨成了猪肝色,几乎喘不过气。两人无声地僵持着,李墨白在一旁看着干着急,心中升腾起一种被遗忘的寂寞感。
他有点委屈,很想不厚道地冲黑衣人说:“那个,这位仁兄,我与你们的恩怨无关,可不可以先放了我,也好安静无干扰地解决你们之间的争端……”
可惜李墨白骨子里还算重情义,实在抹不下这个面子,也不能眼睁睁地看莫风就这样被掐死。他想了想,还是开口劝:“那个,这位仁兄,你别太冲动,让莫风解释一下吧,不能太心急就杀了他。”
后来李墨白想,莫风肯定就是从这个时候就恨上了他。
黑衣人听完李墨白的话,居然乖乖地松了手,莫风终于得到解放,大口大口喘着粗气。黑衣人看着李墨白若有所思道:“你说得不错,我确实不能如此便宜了他,”他的眼神更为狠戾,拍拍莫风的脸:“莫老大当年赠与我的伤我到现在都还记着呢,今日好不容易遇见,我当然要一点点还给你。”
喂!我不是这个意思!李墨白汗颜,不忍去看莫风埋怨的眼神。
这之后黑衣人对莫风实施各种严刑酷打,我们自不必在这一一阐述,只需想象当年的革命烈士在渣滓洞中忍受的酷刑,便可见莫风之凄惨。当然,烈士们是为国捐躯,莫风,或许只是在承受无妄之灾。
与李墨白先前觉察到的一般,黑衣人似乎受过某种特殊的训练,在毒打囚徒方面极富经验且充满想象力。他的下手凶残,力道足劲。比如向着莫风胸口那似足球运动员般的临门一脚,姿势标准,动作快准狠。那一脚下去,李墨白登时听见‘咔擦’数声,心里叹息:唉,这得断几根肋骨啊……
这踢断肋骨也讲究学问,踢断了右侧最下面的两根,极有可能伤及肝脏,剧痛难忍,但短时间没有生命危险;若是上面一些的,则很可能损伤心肺,造成穿孔和大出血,为了还能看见明天的太阳,尽快的手术治疗是必须的。
李墨白不知道莫风伤到哪了,可看他捂着胸口的痛苦神情,黑衣人那一脚,绝对不轻。
这种暴力持续了好一会,李墨白愈发觉着黑衣人的精神并不正常,比如他不时回头与身后的空气交流,如同征求那个传说中的‘小唯’的意见一般。他会指着莫风身上的某处,问小唯:“这里如何?”或者从带来的背包中取出刑具:“这件如何?”侧耳聆听片刻后,似得了上级旨意,毕恭毕敬地如实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