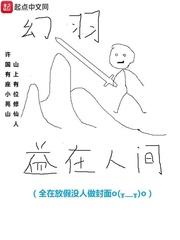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五行神物 > 第30章 灭门(第1页)
第30章 灭门(第1页)
“我说这位客官,你是冒牌商人吧,看你穿的人模狗样的,感情是来本店蹭吃蹭喝来了,想赖账,留下一条腿。”
乌师庐好歹也是草原上的一条汉子,若论杀伐决断,小小年纪不输给他的父亲,取颗首级如套匹马,可是此时却是捏着一枚钱币窘迫无语。
见小二言语刻薄,拍下那枚五铢钱大喝道:“赖什么酒钱,我堂堂……”
话还没说完,乌师庐自知失言,赶快打住。
店小二咦的一声问道:“堂堂?你堂堂什么?我看你就是个混吃混喝的大骗子,少在这摆谱。”
乌师庐一下子气馁了,接话道:“你管我堂堂什么,反正不会差你那点钱!”
此时店内的人都看过来了,店小二和乌师庐僵持在那,
“小二,我想这位客官想必是钱币不够了,就不要为难他了,看样子不像汉国人,是个远路来的,我替他给了吧。”
店小二循着这苍老声望去说道:“哎哟,原来是侯老倌您呐,您可是老主顾了,您要替他给了也行,不然呐,今儿不留下条废腿甭想走。”
店小二故意拉高了声音,对乌师庐讥哂道。
侯老倌是附近放牧的老羊倌,平日里就爱喝这家酒肆的酒,故而与店家相熟,今日店家就不再纠缠乌师庐,乌师庐随即向侯老倌道谢。
侯老倌是个古道热肠的人,见乌师庐一副商人打扮,却没钱付酒钱,想必他是遇到什么难处了,于是便问道:“小伙子,看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是不是生意有什么不顺的地方,这样吧,你身上没钱,如不嫌弃就跟我老倌到寒舍将就一宿吧。”
乌师庐见在汉国喝酒住店都要钱,甚是不习惯,还不如在大草原上逐水草而居来的方便,可是这里毕竟不是草原,既然还有这么好的人,于是就答应了侯老倌。侯老倌付了酒钱,灌满了酒葫芦,就领着乌师庐出了酒肆,朝自己家走去。
侯老倌家是土坯房围成的院落,屋顶盖着茅草,后院挺宽敞,圈着羊,乌师庐先警惕的朝里看了看,才走进院子。进了院子听到羊群咩咩咩的叫声,侯老倌进了自己家热情的招呼乌师庐,侯老倌的儿子孙子都围过来打听乌师庐。侯老倌向大家介绍说这是落难的商客,咱不能有难不帮啊,儿孙们都笑着向乌师庐点点头。
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下去,西北的寒夜冷风呼啸,侯老倌招呼乌师庐到闲置的土房子里歇宿,许是这么多天的颠簸,再加上方才的酒足饭饱,乌师庐一沾床,没多久眼睛上下就开始打架了,迷迷糊糊就沉沉的睡去。
沉沉的暗夜,寒风呼啸,静的出奇,侯老倌一家也无暇多坐,这样的夜里,最好的御寒方法就是钻进被窝做梦。暗夜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游走着,不知不觉天入黎明。
“等会趁他不注意你先摁住他,这家伙肥得很,怕挣脱了。”
“行,要是摁不住,再叫几个人。”
“问问阿四刀磨好了没,这天气洒点热水再磨,就不会冻住了。”
“好嘞,我这就去看看。”
“让他小声点,别把他吵醒了。”
乌师庐这一觉睡得甚好,迷迷糊糊中耳朵听到窗外有动静便醒了。敏锐的听到后院中人的对话,“我就说这侯老倌没那么好心收留我,原来是想诱杀我领赏,哼哼,就凭你们几个还想拿我?”
乌师庐冷哼之余翻身凑近窗户往外看,只见侯老倌的儿子孙子拿绳子的拿绳子,拿棍棒的拿棍棒,正悄悄摸摸准备着。
此时乌师庐伸手到长靴里摸到短刀,啊呀一声掀开窗户飞身而出,睡了一觉,乌师庐精神体力都恢复饱满,行动敏捷。只见他像野狼一般冲向侯老倌的儿子,侯老倌儿子正整理好绳子,听到有人破窗而出,刚转身,就被乌师庐一刀抹了脖子。
惊魂未定的侯老倌孙子一下愣住了,见爷爷领回的商人化身歹人行凶,也顾不得询问就举棒砸来,乌师庐一只手接住棍棒,一只手挺刀刺入侯老倌孙子。
侯老倌孙子恶狠狠瞪着乌师庐,嘴里发出最后一声“为什么?”话还没说完就倒在地上。
乌师庐杀的兴起,心想:“反正已经杀了,既然你们这些汉人想诱杀我,还不如我先下手为强。”于是提刀来到前院,迎面撞上磨好了刀的阿四。
阿四正提着一把解牛弯刀要进入后院,见乌师庐目露凶光,手上有血,一向也杀牲口颇有些胆气的他问道:“这位大兄弟这是要干啥呀?”
乌师庐也不答话,举刀便刺。阿四见短刀刺来,大叫一声,解牛弯刀随即砍过来,只可惜阿四只是使屠夫的蛮力,不懂避让攻击之法,被乌师庐闪身躲过,短刀顺势已刺入阿四心脏,阿四啊了一声,捂住胸口倒在地上。
顷刻间,乌师庐已结果了三条人命,不可谓不凶残,此时走到前院的乌师庐看到侯老倌正急匆匆赶来,手里还抱着一坛子酒,见乌师庐身上沾着鲜血,凶神恶煞,被此等模样惊吓,瞬间呆若木鸡,嘴里战战兢兢问道:“你,你,你这是干嘛?”
乌师庐此时已杀红了眼,本不想解释,但念及这老倌还曾请自己饮酒,便怒问道:“老头,为何以留宿为名诱骗我到此处,还想磨刀杀害我,是不是想割我首级去领赏?”
“领赏,领什么赏?你,你,你难道就是城门楼子告示上通缉的人?”侯老倌战战兢兢,抱酒坛子的手不住地抖动。
事已至此,乌师庐也不再隐瞒,便点点头默认了他就是城墙上贴的通缉犯,“砰”的一声,侯老倌怀里的酒坛子掉地上摔碎了,瞬间酒香四溢,侯老倌只感觉胸口起伏,话说不出来。此时被乌师庐在后院转角处杀害的阿四使尽最后一丝气力爬出来,见到侯老倌正在和乌师庐对峙,从胸腔里吼出一声:“快跑,他是杀人凶手……”还没说完就趴地上咽气了。
侯老倌见状怒吼道:“为什么?为什么?我老汉一生老实巴交,从来没有得罪过人,请你留宿就是看你是个可怜的外乡人,没有半点恶意,今天早上只是磨刀只是要杀一头牛款待你,昨天晚上你睡了以后我们商量好的,所以没有告诉你,没成想你竟然恩将仇报,残杀我家人。”
乌师庐闻听此言,再看看摔地上的酒坛,瞬间感觉自己可能是神经过于敏感,误杀了他家人,眼里的狠劲消退了,可是看着眼前的侯老倌,刚才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如果他去报官,汉军围捕过来,此地是汉地,有重兵把守谅难脱身,于是杀心顿起,对侯老倌施了匈奴礼后道:“感谢老倌的款待,可是事已至此,容不得仁慈了,愿长生天保佑你升天。”
说完,甩出了短刀,“嗖”的一声,短刀刺入侯老倌胸膛,侯老倌应声倒地,手脚挣扎了一会不再动弹,只是眼睛死死地盯着乌师庐,眼里满是不甘。
乌师庐自知犯下大错,可是此刻没有心思悔恨,走到侯老倌面前拔出短刀,拭去鲜血,插入靴子,看了一眼侯老倌,将他的眼睛抹下闭住。然后起身来到后院,倒了干粮,翻身上马,一扯辔头,快马奔出院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