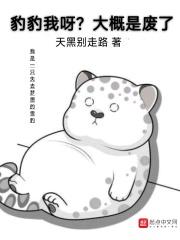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重生之卫七全文免费阅读无防盗 > 第122章(第1页)
第122章(第1页)
老夫人话中竟然带着隐隐感慨及消沉。
便是在精明睿智的老者,也永远都会为底下的儿女操心。
卫臻忙紧紧握着老夫人的手道:“呸呸呸,祖母说的什么劳什子胡话,祖母千秋万代,长命百岁,可不许说此等不吉利的话。”
说着,细细打量着老夫人,见老夫人眉间自待忧愁郁气,心中不由叹了叹,只将鞋袜一脱,难得跟小时候一样爬上老夫人的罗汉床,歪在老夫人身侧,缓缓问道:“祖母可是在担忧二伯。”
说到这里,想起上辈子二伯一生清苦,一辈子遭到众人的不解与埋怨,放佛是所有人眼中的怪物似的,不由叹了一口气,嘴上却缓缓道:“臻儿记得小时候大姐姐十分喜欢一道前菜,便是那种府外老百姓们才爱吃的又腥又臭的松花蛋,寻常有些台面的女儿家都不爱,只觉得有种腐烂般的怪味,十分上不得台面,府里唯有些个老婆子或者乡下来的小丫头们才吃,大姐姐竟也喜欢,当时竟然还招待给几位妹妹们吃,结果六姐姐跟九妹妹见了一脸嫌弃,就连臻儿也用袖子遮面捂鼻,只觉得那味道十分刺鼻,所有人都一脸嫌弃,臻儿甚至记得当初六姐姐问了一句‘此等腥臭之物,大姐姐如何咽得下去’,结果祖母猜大姐姐当时冲六姐姐回了句什么不曾?”
“回了什么?”老夫人原本阖这双目歪在软枕上,闻言,忍不住睁开眼看向卫臻。
卫臻一本正经道:“大姐姐冲六姐姐说‘彼之砒、霜,吾之蜜糖’。”
说到此处,卫臻语气微缓,抬眼看了老夫人一眼,见老夫人神色微愣,卫臻又忽而道:“今日臻儿听了二伯的事儿,一如小时候对大姐姐喜欢吃那等腥臭的松花蛋一事一样不解,可是臻儿因未曾吃过松花蛋,便也不好对松花蛋有任何评论,正如臻儿未曾经历过二伯那般丧妻之痛,也无法理解二伯缘何有那等荒谬的想法,可是,臻儿却知,二伯这般选择定有二伯的理由在里头吧。”
卫臻耸了耸肩,缓缓道。
老夫人听了卫臻的话沉默良久,只捏了捏卫臻的手,微微叹了一声,良久未曾说话。
卫臻便也不再多言,老夫人是何人,她活了大半辈子,自然无须卫臻来跟她讲解大道理,只是,但凡是人,便是再完美厉害之人,也永远有无法理解的事或人,二老爷想要出家的想法虽荒唐荒谬,可荒谬得过卫臻的死而复生么。
重来一世,很多事情,很多执念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了,正如前世卫臻对太子的宠爱,对卫绾的仇视,对权利对荣华富贵的执念,到了这辈子不过烟消云散,早已无影无踪。
她重活一世,尤其是历经五年前阮氏的生死大战,到如今,很多事情都看淡看透了。
然而依然有很多人就是迈不过那道心里防线,正如二老爷对妻子的死久久无法释怀,正如世人包括大老爷、老太太对二老爷这种至亲依然对他的这个荒唐想法永远无法接受,其实,有什么不能接受,就像那句话,汝之蜜糖彼之砒、霜,然而或许正是因着有这些分歧差异,才会令世人有千种万种,令世事不尽相同,令整个世道奇妙无比、五彩斑驳吧。
那晚,卫臻陪了老夫人许久,临到用晚膳时,周妈妈见老夫人情绪不佳,气色不好,过来细细询问道:“今晚给老夫人备用了一些粥类细软食物,老夫人多少起来用点吧?”
却未料,只瞧见老夫人冷不丁挣扎着起来了,卫臻立马跟着起了,亲自侍奉老夫人下榻,只听到老夫人缓缓道:“那个叫什么松……松花蛋的,来一份尝尝味吧。”
卫臻听了一愣。
不多时,只见老夫人挑了挑眉,冲她淡淡的笑了笑,不过片刻,脸上的郁气已是消散了不少。
周妈妈见了,忙亲自去厨房吩咐了,高兴得连走路都带着风,临走前,朝卫臻投来了一道十分感激的目光。
卫臻冲其眨了眨眼。
作者有话要说:二更比较晚了。
当日,打从荣安堂出来后,卫臻便又马不停蹄的去了秋水筑。
原本自打五年前那事后,老夫人重新指了一处住处给阮氏,让其搬出秋水筑,可彼时阮氏在秋水筑住了七八年,她跟卫臻所有的回忆全部留在了秋水筑,并且,在这里,还曾有过一个孩子,阮氏最是心软念旧之人,如何都舍不得搬走。
直到两年前谭氏随着五房一道回京,老夫人便将整座秋水筑一并指给了阮氏,阮氏便将东西厢房两处院子一并打通,合成了一个单独的院落,阮氏特意给卫臻安置了一间屋子,自所有人走后,老夫人也并未曾拘着她,她总是荣安堂、秋水筑两边跑,今儿个在这个院子住上两日,明儿个在那个院子住上两日,每日清闲自在,再也没了以往的糟心事,这样的日子一过便是两年,舒心爽快,若是允许,卫臻愿意一辈子就这么过下去。
然而,人生并不能暂停,无论你乐不乐意,永远都必须向前走,去历经那些必须要历经的苦难、逆境,唯有翻过了满路荆棘,方能走向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
卫臻来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她在老太太院子里用了晚膳的,此番到了秋水筑远远地只见院子里透亮,想来阮氏还在等着她回来再用一次吧
每每她都要用两次晚膳,陪完了老夫人还得陪阮氏,以至于她如今都十一了,要到了抽条的年纪,身子倒是长高了,大约是这辈子营养跟上来了,比前世高了不少,可脸上依然肉嘟嘟的有些婴儿肥。
到了院子口,远远只见紫屏在院子口候着,见了卫臻,立马恭恭敬敬的迎了上来,道:“小主子总算是来了,姨娘一直等着您了,饭菜都要凉了。”
卫臻晓得阮氏是个什么德行,每每怎么劝也不听,总是要等到卫臻来了跟她一道吃,不然如何都不动筷子,自从五年前那桩子事儿后,阮氏是将卫臻看得越发重了,只眼珠子似的不错眼的将她守着护着,一日没见,心里就七上八下的,生怕她出了什么事儿。
卫臻知道她心里落下了阴影,便也一直形影不离的陪着。
边往里走,边问行礼等事宜都安排得怎么样了,紫屏道:“一早便收拾妥了,只不过……”
紫屏耸了耸肩道:“姨娘约莫是舍不得走了,恨不得将整个院子都给搬空了才好,今日儿一个人坐在屋子,将每样东西都摸了个遍,一脸不舍,奴婢几个都不敢打扰。”
五年前,殷氏将整个秋水筑的下人全部发卖了,除了雯烟,一个未留,然后托人牙子重新从市口挑了一批供秋水筑亲自挑选,这些下人全部都是经过卫臻亲自一个一个挑的,卖身契全部捏在了阮氏手中,完完全全归她使唤,后卫臻又将她跟前的紫屏与绿蕊一并送到了秋水筑,老夫人见卫臻跟前缺人使唤,便又将她院子里负责洒扫跑腿的杏丫给了她。
如今整个秋水筑上下被雯烟管束着,又有紫屏、绿蕊相助,整个秋水筑围得跟铁桶似的,阮氏身边再也未曾出过任何事儿,可卫臻却觉得这几年来,阮氏过得并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