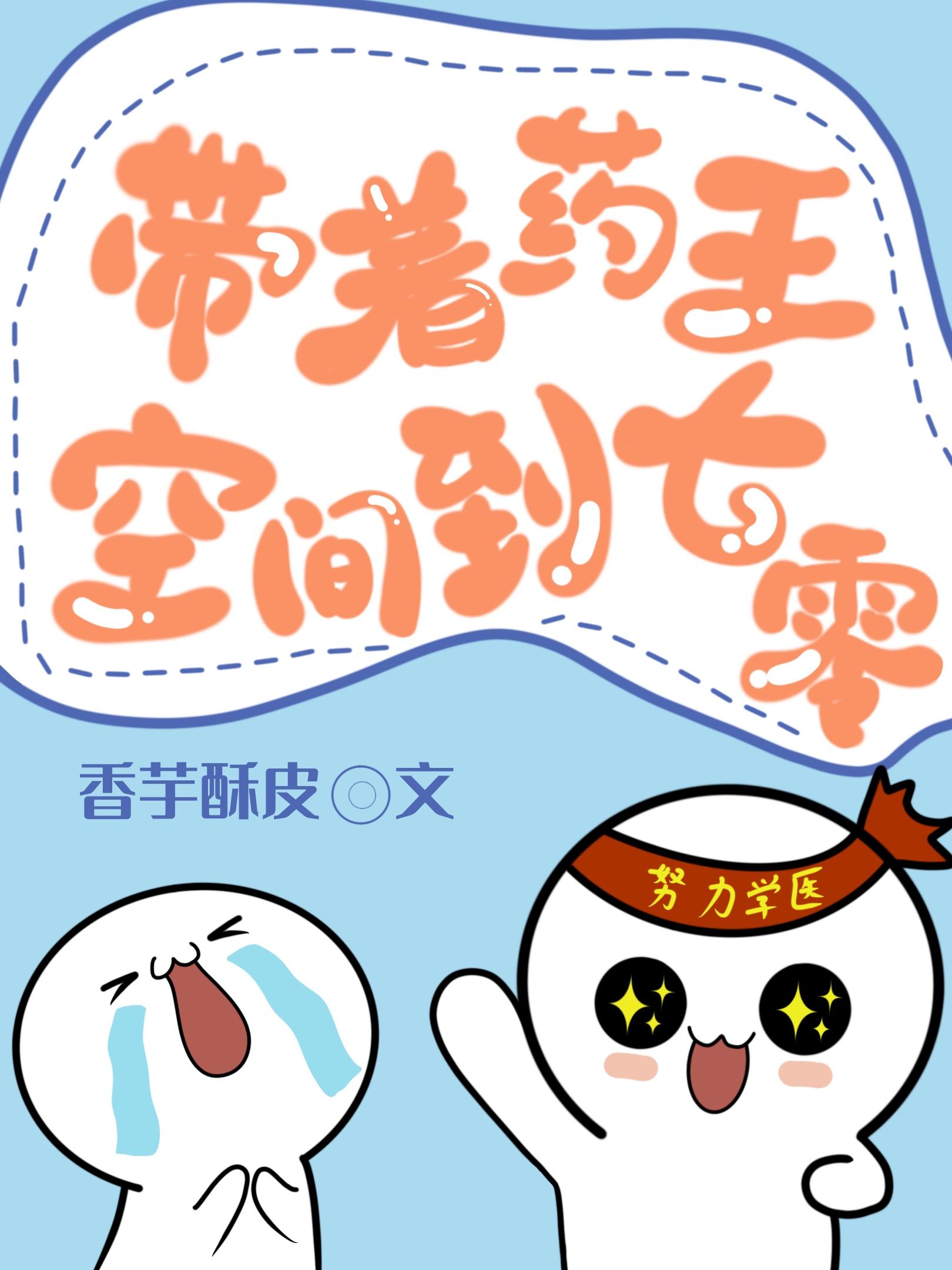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齐家安宁蹦得高 > 第9章(第1页)
第9章(第1页)
这个村庄人口适中,很团结,一群壮汉把陈三狗他们堵在了村口。
荒年不易,因着村里有口流不干的活泉,他们村才难得没散,但也仅限养活村里的人了,故而村子成立了巡逻队,每夜换班巡逻,防止有外人潜进来偷水。
为首的村长精神矍铄,双眼冒着精光,看眼前这群人披头散发、衣不蔽体,明显是遇到了不测,救助他们大概率讨不着好,说不定还会浪费村里的资源,于是捻着胡子劝退他们:“你们快走吧,再往前就能到镇上,留在这儿只会浪费时间。”
他身后的大汉们举着锄头木棍,目露凶光。
可是陈三狗知道他们每个人都已经精疲力尽,老弱病残孕占了他们一半人,怎么也没能力走到下个落脚的地方了。
他从腰间摸出个发簪,说:“您行行好,我们就休息几晚,等老爷醒了就走,若是您愿意,这发簪就送给你们,作为我们的暂住费用。”
这是老太太见面时给他的那根银簪子,做工精良。但他本是个男孩,只觉得簪子金贵,却不喜欢往头上插戴,土匪搜罗衣裳首饰时,他穿着朴素扎着雀尾,土匪以为是个小厮,这根藏在他腰间的发簪就没被发现。
村长见着簪子,眼里精光更盛,他转眼又看向驮着江老爷的高头大马,眼珠子一转,说:“我看这马也不错。”
陈三狗被噎住,他不是什么能言善辩的人。
不过幸好有个伶牙俐嘴的杨秀荣,她是商户出身,见家里父兄做生意惯了,本能地就上前讲:“这簪子可不便宜呢,这做工放在金城里都是上等的,即使您看不出,也能看出材料是纯银的吧?买下你们村一座房都绰绰有余,只住你们这几天都是便宜你们了,实在不行我们就多走几步去镇上,在客栈打了尖,十天半个月总是住得的,要不是正好撞上你们村,这个便宜还轮不到你们占呢!”
这村长在村里算一号人物了,可遇上从金城来的商户出身的杨秀荣,那就不够看了。
这么一通叽里咕噜的豆子倒下来,砸的村长耳朵嗡嗡的,生怕放走了便宜,面上却还装着吃了亏,说:“那就这样吧,村口西边那个房子空着,你们过去就行,可说好了等人醒了就走,死了也得走。”
村长自觉考虑精明,占了个大便宜,殊不知杨秀荣也是夸着往外说,那簪子好是好,实际上根本买不了一座房。
幸亏这村子的人除了村长以外都还算纯良,不然以这荒年的景象,他们拿出簪子,怕不是要再被抢一次。
杨秀荣也装着吃亏,哼了一声说:“便宜你们了。”
交完簪子,一个大汉领着他们到了村长口里的那座房,没人住是有原因的。
整座房三间屋,除了正屋还算完整,两座侧屋一座全塌了,一座房顶破着大洞,根本住不成人。
送他们来的大汉见他们老的老小的小,晕的晕孕的孕,想起自己家里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感慨万千,好心给他们送了一大堆稻草,一行人在正屋铺好了,顾不得男女大防,挤在一起捱过这个难熬的春夜。
江家的主子们没睡过稻草,除了周大雨和陈三狗,都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第二日都挂着两个大黑眼圈面面相觑。
杨秀荣是孕妇,饿不得,推了推不停挠身上的江子德:“你去弄饭来。”
晕着的老太太适时转醒,还没看清周遭环境,就被抓住救命稻草似的三爷一嗓子吓住了。
“母亲!”三爷虽是二姨奶奶生的,但自小就跟老太太这个给他发月俸的正室母亲更亲。
“母亲您可算醒了!您可不知道儿子都担心坏了,您快想想办法吧,咱们一家老小等着您拿主意呢!”
三爷说是小,却也已经17了,被叫了几年的三老爷,却没一点“老爷”的担当和责任。
老太太遭受惊吓,差点又撅过去,二姨奶奶连忙过去搀住抚了抚她的心口,她这才定住了神。
弄清楚情况,她强撑起来,在自己头上摸索几番,抽出几根拉得细长的金丝银丝,打眼看去还以为是或黄或白的头发,藏的好,没被土匪搜着,这是她娘教给她的,是金城大户人家防身的手段。
“大雨,你去村子里,买些吃的来,三丫,你会骑马,去镇上请个大夫,其他人,跟我一起,把屋子收拾出来。”
三爷不堪用,周大雨人高马大,在村里不会被欺负,陈三狗面善会骑马,大爷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三太太也快生了,留在此地是最好的选择,老太太迅速判断形势,给每个人都分配了任务。
汪琦生在出过宫妃的大家族里,自小金枝玉叶地养着,一生除了丈夫是个三心二意的浪子之外没遇过不顺,临到老却碰到这么一遭,确实非常愕然意外,却并不怨天尤人,在过了最初的冲击后,重新恢复了作为一个大家族老夫人的果决明断。
时与命,皆是船下的浪,即使风吹浪大,掌舵人冷静判断,抓准浪之间的缝隙,船也能安然穿行于风暴间。
此刻她的儿子还昏迷着,那就让她这个副手先顶上!
男扮女装
为了方便出行,陈三狗穿了一套三爷的衣服,“女扮男装”。
老太太汪琦夸赞他:“你眉毛浓,身量也长,这么一扮,像个真正的男儿郎了。”
陈三狗红了脸,想坦白他本就是个男孩的话滚到了嘴边,被老太太拍在背上的手掌拍散了。
“快去快回,我们等着你。”
“嗯。”
陈三狗不再犹豫,翻身上马,一身绸缎长袍被他拉起来围在腰上,成了身适合骑马的劲装,衬的陈三狗英姿飒爽,打马披风少年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