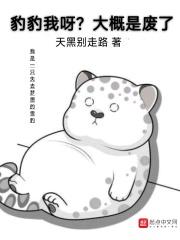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太子饲养手册 > 第42章(第1页)
第42章(第1页)
宋衍迷茫地看了他一眼:“?”柳泽见他似乎真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伤人家小姑娘心的事,恨铁不成钢地说道:“殿下,您刚才做什么说那话?”宋衍越发不知所措:“本宫的意思是,她既然是谢家的人,知道这些也无妨——总归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况且别的不说,本宫堂堂一国太子,护个她还是不难的。”柳泽盯着他看了几眼,见他神情眼神不似作伪,暗自叹气,心道:“那你倒是说出来呀,让人家猜什么哑谜?”然而他再怎么想帮宋衍补救,也无济于事了。谢毓自那之后一直躲着宋衍,若是非要让她送点心来,便称病,不知道“病”了多少回,才让宋衍确信,这小姑娘的确是不想见到自己。这一躲,便躲到了长安的第一场雪。江南不常下雪,年节的时候谢毓一向会留在家中,因而“雪”这玩意对她来说,一向是件新鲜玩意。早上起来,便看见外面落了薄薄的一层白霜,用靴子踩上去,能留下一个清晰地印子。瑞雪兆丰年,这场雪,对大梁上下的老百姓,似乎是个好兆头。谢毓觉得有些冷,回去多加了件披风,便见白芷蹦蹦跳跳地过来,远远地喊道:“阿毓!我听说晋王殿下今天要班师回朝了,大军下午便到皇城!”谢毓理了理自己堕马髻上的碎发,轻声说道:“喘口气再说。怎么这么突然?”“契丹跟我们求和了,边关用不着晋王殿下驻守,便提前回朝了——据说延臣宴上还会有契丹使者来上贡。”白芷的脸跑得红扑扑的,眼中满是八卦:“你和那个戚槐一天到晚通信,可商议出什么成果来了?”谢毓“唔”了一声,说道:“点心都定下来了,只是其中一道我们都未曾做过,若是贸然下手,怕是做不好。”白芷:“竟然还有你不会做的点心?叫什么呀?”旁边的梅花枝承受不住雪的重量,微微颤抖了几下,冰晶洋洋洒洒地落在谢毓身上,水红色的披风上白白地一团。谢毓将雪拍干净了,说道:"说是北方的点心,叫面果儿。"南方人的舌头是平着长的,她这么硬拗出来的一个儿话音,颇有点四不像的意思。自古北方吃面,南方吃米。面果是北方贵族才能用得起的佳肴,讲究个“形似”,用面做成的果子,要和真果子一模一样。这可不是什么容易事儿。谢毓将披风上的兜帽笼在头上,只留下一个尖俏的下巴在外面:“冯公公说,这种技术的传承者正巧在长安城,我出宫去讨教一下。”她朝着白芷稍微点了下头,就急急地走了——宫禁的时间不晚,她要赶着出去,不然跟人家都说不上几句话。皇帝给她的牌子是纯木的,没太子爷的那块显眼,但好用许多,往身上一挂,宫禁对她而言基本就是个摆设。守门的侍卫对她眼生,见她穿的私服,兜帽低低地压着,也看不出来到底是几品的宫女,便笼统地叫了声“姑姑请”,放她出去了。谢毓叫了辆马车,疾驰到了外城。外城住的都是商户、百工和寻常百姓,虽说已经入冬,倒地是天子脚下,四处还是一片热闹景象。谢毓许久没有出宫了,有些新奇地看着外面。卖炊饼的汉子家家户户地叫买,街边的茶馆里弥散出粗茶的味道,穿着寒酸的读书人在里面拿着陶碗高谈阔论,商铺家的孩子穿着臃肿的棉袄,在官道旁边玩耍嬉戏。雪逐渐地又下起来了。谢毓给了那车夫几钱碎银,跳下车去,发觉脚下的触感又软和了几层。那位老厨子的住址在东市西边,马车在巷子里不好走,谢毓便在务本坊下了车,准备徒步走过去。少了马车车厢的遮挡,冬日的风还是有些凛冽的。谢毓的嘴唇被冻得发紫,连忙加快了脚步。“宣阳坊43号是这儿了。”谢毓抬头,看见了座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房子。遮风避雨足矣,但没有一点富贵气,实在不像是一门手艺的独传弟子住的地方。房中空空荡荡的,院子落了锁,房主人大约是出去了。谢毓左顾右盼一番,见旁边有几个孩子在玩闹,便将兜帽拿下来,笑着往其中一个手里塞了块饴糖,问道:“小儿郎,你可知道住这里面的姓李的爷爷在哪里?”那孩子吮了下手指头,用衣袖擦了下鼻涕,呆呆地看着她,也不作答。谢毓有些不知所措,正想再问,却见远处虎虎生风地走来了个用蓝布扎着头发的大婶。那大婶一把捞住了孩子,朝着谢毓一挑眉,眼里满是警惕:“你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