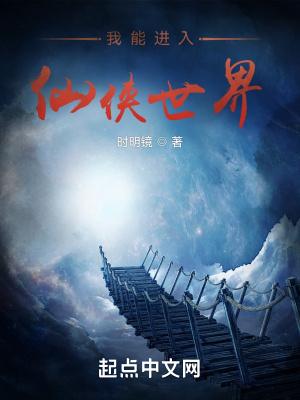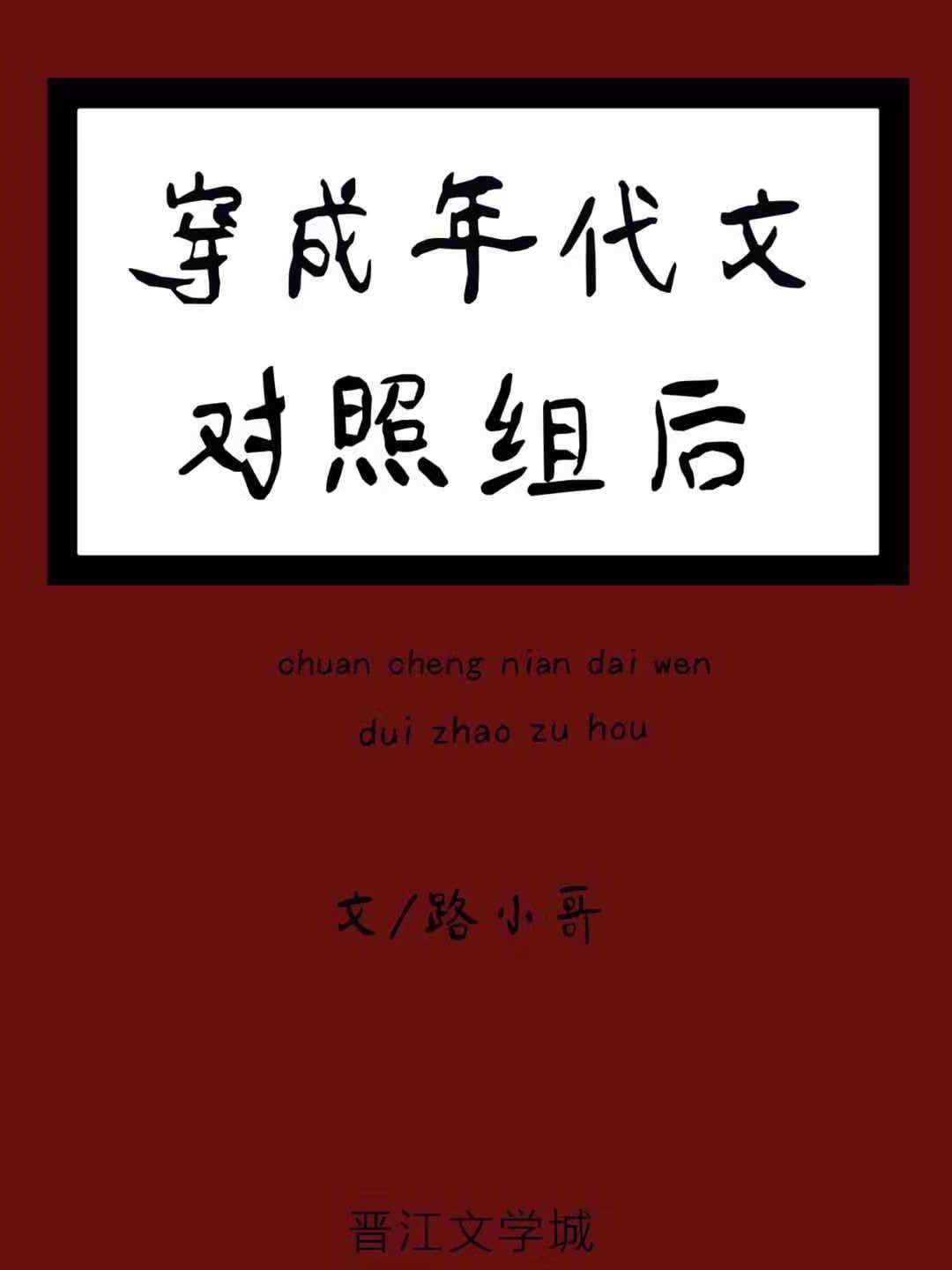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云间草堂清茶馆(泰晤士小镇店)怎么样 > 第一百九十九章 离魂未安风凉起(第1页)
第一百九十九章 离魂未安风凉起(第1页)
何胜军的灵堂设在何平家的客厅里,客厅面积约莫四五十平方,两侧分别连着两个小卧室和一个锅炉房,只是里面的锅炉早就已锈透,根本无法使用。整个房子只有客厅靠近大门的地方搭了一个临时小铁炉,终日烧着煤炭,这个唯一的火源也成为守灵人和众多吊唁人闲聊取暖的汇聚之地。
炉子很小,周边放了几个高低不等的凳子,最多只能同时坐下五个人。因此宾客们来来往往不停轮换,只有何文何朵全天候都守在这里。
听到姑姑和三婶的污蔑,何朵怒火中烧,不忿地说道:“声音这么大,生怕我们听不到啊?亲不亲是旁人能评判的?喊的声音大了就是亲,不喊就是不亲,我们跟我爸亲不亲你们平日里看不到吗?”
何胜果看侄女这义愤填膺的样子,知道这家伙飙起来了,只是她也不打算退让,语气柔和但坚定地说道:“咱当然知道谁亲谁不亲,但是人家别人看不到啊!这么多亲戚邻居来吃席,看的就是你们哭熄火,这是习俗。不好好哭,丢人哩,人家都笑话你爸哩!”
何朵气急败坏,却也不便继续争执,说道:“真不是不想喊,是真的不会!本来就伤心的很,却偏要思考怎么哭喊才正确,这一思考,精神就分散了,想的都是怎么表演,还咋哭呀?而且哭喊的都是土话,真的投入不进去呀!但是用普通话又更奇怪……太难了啊!”
“文文你哭,朵朵不行,你哭出来。你是老大,你要做好样子。”何胜果不再搭理何朵,而是威严地命令着何文。
见姑姑并不打算继续搭理自己,何朵也懒得说话,烦躁地走出屋外,晃悠到隔壁屋母亲那里。
母亲的卧室里依然乌压压挤满了亲戚,一则是天气太冷,人多了挤在一起总有些热气,二则人们也可以随时安抚许娇兰这个老弱的女主人。何朵一看这屋里的架势,留下来既没位置也有些尴尬,立刻走的话又有些不好看,便随口问道:“妈,见着我的杯子了吗?”
“没有啊,外头有吗?”许娇兰迷瞪着眼睛四处看了看。
“哦!”何朵作势便准备离开。
“重新倒一杯好了,来,朵朵。”一个亲戚叫住了何朵,殷勤地取来纸杯,给何朵盛了些大壶里的粗茶水。
“坐这儿喝,来,挤挤,暖和点儿。”另一个亲戚热情地拉何朵坐到自己身边,旁边挨着的几个女人也纷纷挪动着位置。
何朵这下反而不好意思立刻离开,只得微笑着应和两声,端着纸杯暂时坐定。
“你家朵朵真是个好姑娘,你爸你妈有你,这辈子值了。”
“是啊,娃多孝顺啊!给你爸看病看了一年,一个闺女家在那么远的地方忙里忙外的,真不容易!就这能力和孝心,试问现在几个做儿子的能比得上?”
“姐啊,你可就舒心吧!以后安安心心照顾好自己,也算是解脱了。”
房间里都是表姐表姑姨姨婶婶堂嫂堂奶奶等人,是爸妈双方的亲戚辈们。其中一些人住的离老泉村近,何朵还大体对的上脸。一半以上住的远、以前来往少的,何朵只是看着面熟,却不大喊的出来称呼。不过家里头办丧事,终究不是什么认亲的开心场合,何朵不一一称谓致意,人们倒也并不介意。只是大家说的说的,话风就突然转了。
“朵朵,你这给你爸看病,花了多少钱?”
“嗨,没仔细算过。”何朵笑道。一方面自然是应付众人,另一方面她的确也没仔细盘算过。
“三四十万肯定有的。”
“哪里够?东东说至少花了七十多万。”
“不是听说一百多万吗?”
七姑八姨们一提到钱,眼里纷纷放着亮光,还没等何朵说话,已经七嘴八舌热烈讨论了起来。
何朵笑着瞅了眼母亲,见她也有些恍惚,心知应该是三叔和堂弟们的谣传。脑子里正盘算着怎么离开,一个亲戚突然亲昵地握着何朵的手,说道:“朵朵,你这一年赚多少钱呢?”
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人们迫切又紧张地等待着,想亲自见证何朵这个传闻中的女强人亲口告诉他们,那一串只在茶余饭后出现的“天文”数字。
何朵调皮地笑了笑,说道:“没赚多少。”
“百八十万总有的吧?”立刻有人迫不及待地追问了起来。
“哪有?我又不是开矿的,哈哈!”何朵笑着跳下了炕沿。
“四五十万肯定有的了。”
“瞧你们说的,混口饭吃而已,没多少的。”何朵应付道。
“哟,真厉害啊!我这辈子都没人家朵朵一年赚的多!”
“一个月有多少?”
何朵笑而不语,脑力里火盘算着怎么应对,好在这时刘璐可的电话突然打了过来,何朵如逢大赦,“喂”的一声,无比正式地接通了电话,正大光明“逃”出了屋子。
“何朵,你爸爸的事情我听说了,你还好吗?”刘璐可关切地问道。
“还好,没事,放心。”何朵说道。
“我也不知道能说什么,现在这个时候,语言都是无力的,只能劝你尽量节哀。”刘璐可轻轻叹道。
“没事,最痛苦的那两天已经过去了。”何朵一边走向院外,一边说道:“村里人说,人死后的前三天,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的。前面的几天,我们自己也感觉我爸还高高兴兴地和我们在一起,感觉他正高兴地看着这么多家人团聚,听我们说玩笑话呢!死这件事情,我们的感觉都没那么清晰。而且我爸从去世到下葬要等七天,七天里每天都有村里人和亲戚来一起帮忙和吊唁。我们都忙着招待客人,忙着操心灵前的很多礼仪。一忙起来,连伤心都不能聚精会神,反倒一下子没那么难过了。”
何朵站在院边,回望着杂乱不堪人来人往的院子,有种不真实的抽离之感。
“那就好,那就好,所以老一辈里很多规矩都是有它的道理的。”刘璐可说道,语气也松弛了一些。
“我也总是会忘记爸爸已经死了。这几天来,守在这里,总感觉我爸还活着,感觉他能看到、听到我们在说他。”何朵一个错愕,悲伤之情又涌了上来。这几日来哭哭笑笑、笑笑苦苦,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