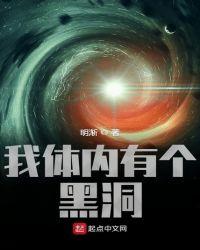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民国遗事1931笔趣阁 > 第73章(第1页)
第73章(第1页)
二人并排坐在后座上,傅靖远今天特地让人给荣祥找了身长袍马褂穿上,因为质地是丝绸的,光滑柔软,穿在身上,不禁锢的难受。现在荣祥的皮肤已经变得很易磨伤,他不晓得疼,给他洗澡的阿妈粗心的很,也不曾留意。还是小孟那天发现他腋下一片红肿,几乎快要化脓,连忙清洗擦药,却始终不见好转。事前谢廖沙嘱咐过,那天不要让荣祥吃早饭。所以在车上傅靖远不住的摩挲他的腹部,总觉得瘪着,担心他饿得难受。虽然他知道,荣祥已经很久都不知道饥饱了。抵达医院时,荣祥还很安静,谢廖沙先照常例给他量了血压,顺便又看了看眼睛舌头,然后抬头对傅靖远道:&ldo;荣先生的喉咙有些发炎,要打消炎针。&rdo;傅靖远连忙转向荣祥,抬起他一条胳膊,一边捋起衣袖一边柔声道:&ldo;是消炎针,喉咙肿了。&rdo;荣祥翻了他一眼,任谢廖沙将针头点在上臂,针尖刺入,他忽然偏了头,对傅靖远一笑,嘴角柔柔软软的翘起来,露出一口细白牙齿:&ldo;你怎么一头的汗?&rdo;脸上是笑着的,声音却颤抖清冷。傅靖远也笑了,抬手摸了摸荣祥的头,新剃的,短到只剩一层乌黑的发茬儿,荣祥素日最恨这种乡下小子似的发型,这次也不例外,但只是懒洋洋的皱了下眉头,示意不满。手中的头温热、又有点茸茸的,因为发丝细软,剪得再短也不至扎手。眼望着麻醉剂被缓缓注入他的体内,傅靖远暗暗松了口气,将手慢慢滑至他的后颈,颈子已经细瘦到了极致,幸好有个小立领儿遮住,否则瞧起来,正是一个细脖子挑了个光秃秃的脑袋。打完针,谢廖沙起身,籍着召唤看护妇过来收拾注射器材的功夫,向傅靖远使了个眼色,傅靖远心领神会,又找出许多闲话,同谢廖沙攀谈起来。荣祥呆呆的坐在一边,先是神游天外的样子,忽然身子一歪,傅靖远连忙扶了他,心道这药效终于发了,正想若无其事的继续自己同谢廖沙的闲聊,谁知荣祥反手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一双清凌凌的眼睛中光亮骤然闪过:&ldo;这不是消炎针!&rdo;傅靖远一愣,随即笑道:&ldo;你是坐乏了,咱们马上就回家好不好?&rdo;荣祥青白了脸色,嘴唇似乎都有些颤抖,却咬了牙说道:&ldo;我……我还有话同你讲,你再给我一点时间……&rdo;傅靖远抬手搂了他的肩膀,声音里还带着极坦荡的笑意:&ldo;回家还有好多时间,不急在这一刻。&rdo;心里却是一动,荣祥显然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用意,可是,他要对自己说什么呢?二人相处这么久了,他到底藏了什么话?&ldo;不……靖远你……&rdo;说到这里,只见荣祥身子直直的猛然向后仰过去,就此昏迷不醒。旁边的看护妇是个胖大身材的白种女人,挽了雪白袖子,粗壮手臂伸过来,一边轻声咕噜了一句,一边从傅靖远怀中把荣祥扯出来,连拉带拽的扶到一边的轮椅上。谢廖沙立起身,向傅靖远点点头道:&ldo;让萨拉带他去一间隔音的治疗室,你可以放心。&rdo;傅靖远意意思思的也站了起来,眼看着那山一样的萨拉把荣祥推了出去,恨不能一起跟上:&ldo;那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他最近身体状况还是可以的……&rdo;谢廖沙背对着大窗,阳光中他的白脸显得有些虚无,连下颏上的金色短须也煌煌然透明起来,只有声音还是真实的:&ldo;傅先生,如果你是宗教徒,那么这些天可以去祷告,请求神的眷顾。&rdo;傅靖远在裤子上,无声的蹭掉了手心中的凉汗:&ldo;是的。&rdo;他苦笑答道。七天,过的好像七年。傅靖远从第二天开始便表现的有些歇斯底里。他站在治疗室的门口,治疗室的铁门上并无玻璃窗子,他只好竖着耳朵倾听里面的动静。连续几个小时,姿势都不会变一下。他是什么事都顾不得了,只想着荣祥一个人。直到第六天,家里的一个小子气喘吁吁的跑来医院找到他:&ldo;二爷,城北公馆来了个老妈子,说什么荣家太太难产了!&rdo;傅靖远缓缓的抬起头,脑子有点发木,张开胡子嘴呆呆的反问道:&ldo;啊?&rdo;&ldo;荣家太太啊,住在城北公馆的那位,大肚子的!&rdo;还是半大孩子的小佣仆喘得说不连贯,又用手在肚子上比划了一下,表示大肚子:&ldo;难产,送医院去了!&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