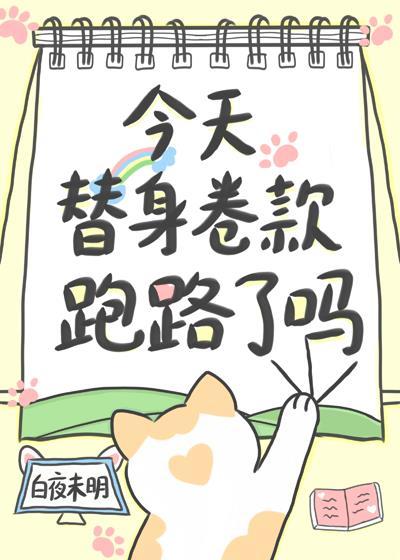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我的竹马是渣攻全文无删减 > 分卷阅读65(第1页)
分卷阅读65(第1页)
眼,他心里莫名一抖,仓促地转开。再用余光瞥时,只看到他们进电梯的背影。
叶开拽着书包带子沉默,惊喜过后,他察觉到一点迟缓的尴尬。
他说:“又涵哥哥,我骗你的——”“帕尔玛没有花语,我瞎编的。”陈又涵笑:“编得不错,我当真了。”叶开轻轻地“啊”了一声,无所适从,嘴硬说:“我、我是要送给那个姐姐的,你觉得怎么样?”陈又涵单手插在裤兜里,笑出声,笑得低下头:“姐姐应该会很喜欢。”叶开观察他的神情,自顾自不高兴起来:“你不是不让我早恋吗,你笑这么开心干什么?”陈又涵双标地说:“我觉得姐姐可以。”靠。
思念如潮水般退却,他现在生气了。
陈又涵意有所指地问:“怎么,抛下外公外婆提前回来,都是为了那个姐姐?”叶开冷酷地说:“对。”二十八层到了,陈又涵按指纹解锁,吊儿郎当地回:“哎呀,好失望,我还以为你为我跑回来的。”“你想得美。”叶开说:“我只是怕回家挨骂,在你这儿躲躲。”门咔哒关上,陈又涵意外地回头:“你爸妈不知道?”叶开扭过头:“不知道。”至于能瞒多久,取决于兰曼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和瞿嘉通电话。
陈又涵盯着人看,把人很不礼貌地堵在玄关,继续揣着明白当糊涂:“那你准备干什么?找那个姐姐?”语气一变,戏谑得说:“你不会要私奔吧?”叶开脸一下子有点红,身后是门,前面是气定神闲压迫着他的陈又涵,浅灰色的玄关有十来个平方,但他无处可躲,硬着头皮说:“姐姐很忙,我不能去打扰他。”陈又涵轻笑出声:“我不忙,你打扰我吧。”叶开怔愣:“啊?”“我帮那位姐姐暂时照顾一下你,别客气。”这才舍得放叶开进屋,埋汰人:“这花快递过来有点不新鲜,我看得洗一洗,都有味儿了。”叶开摘下颈枕砸他:“你闭嘴!”狐疑地抓起t恤前襟嗅了嗅。
疑神疑鬼地想,可能有点飞机机舱的味道。
那也不能算难闻吧!
陈又涵握着水杯笑不停:“你闻自己干什么,你是花吗?”叶开彻底无语,打开行李箱翻出衣服,气得要死地进浴室。洗过澡出来,带着未尽的凉爽的水汽。他擦头,陈又涵给他递上一瓶巴黎水,说:“帕尔玛怎么是橙花的味道?”自己在浴室里放橙花精油沐浴露,好意思拿这促狭人。
叶开没好气地接过水:“长歪了!嫁接了!杂交了!”喝完半瓶水,自觉地去收拾行李。陈又涵给他让出半拉衣帽间。屋子大什么都好说,唯一问题就是客卧的床还在路上,可能在漂洋过海,反正没到海关。
叶开整理衣服,陈又涵抱臂倚着柜门,闲聊般地说:“我只有一张床。”动作应声而停,叶开转过头:“客卧没床?”“有的,就是这会儿可能还在大西洋。”叶开:“……”他的心砰砰直跳——什么鬼!
要留下来吗?还是住酒店?为什么不乖乖回家呢?回了家也可以来找他玩……陈又涵说:“你嫌挤的话——”“我不嫌!”啊,回应得太快了。
叶开条件反射地闭上嘴,仓促地转开视线,听到陈又涵慢条斯理地说完后半句:“……我可以睡沙。”叶开顺水推舟:“那好吧。”陈又涵勉为其难:“那就挤一挤。”……妈的,又撞车。
现场惨烈。
叶开心慌无语,把头埋进衣柜里假装收拾衣物,乱七八糟地说:“我、我都行!”陈又涵失笑:“我睡沙,你睡床。”他第一次意识清醒地睡在陈又涵的主卧。床品都换了新的,窗帘没拉全,淡淡的光影透进白纱漫在地板上,像水。
叶开睁着眼睛数羊,接着就听到客厅传来一声重物落地声——砰!
他受惊地一抖,想到了什么,立刻跑出去打开射灯,看到陈又涵扶着脑袋从地上爬起来,一脸懵。那嘴型分明要骂“操”,见道叶开的那一刻硬生生堵在嘴边,心里想,妈的,丢人。
叶开有点幸灾乐祸:“三十岁神经意识就退化成这样了。”陈又涵抓起毯子,脸色有点臭。
叶开很懂事地说:“又涵哥哥,其实我们可以睡一张床,我睡觉很老实的,不会乱动。”见陈又涵没吭声,他又说:“你明天还要工作,一直睡沙的话会休息不好。”陈又涵仍没吭声,他以退为进:“你不会嫌弃我吧?那我明天回家好了。”陈又涵摔下毯子,揉着肩胛骨骂骂咧咧地跟他进卧室。
半边床下陷的感觉很明显,前所未有地深刻传递出陈又涵躺在他身边的事实。叶开半边身体紧绷,好像肌肉和神经都忘了如何放松了。
这么高的楼层听不到深夜的车声,可他耳边总响起车轮划过柏油路面的刷刷声,在路灯的照射下,马路是明黄色的,可能还会有一点树影,如果起风了,影子便会晃动——“又涵哥哥?”他轻声。
回应他的只有绵长深沉的呼吸。
睡着了。
他小心翼翼地挪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