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楠文学网>荒唐王爷怎么加才艺 > 第159章 定罪(第1页)
第159章 定罪(第1页)
“杨立兆,咱们升官了!”韩士承捧着浙江送来的任命书进了杨立兆的办公室,一本红底蓝字的册子,一个金色的台卡。
杨立兆笑容满面地接过台卡,用衣袖抹了抹,然而上面并没有灰尘,擦拭完毕后如珍宝般小心谨慎地摆放在办公桌上,神情严肃地接过韩士承手中的册子,翻开后,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深深的钢印,外交部副部长的官是多大,杨立兆自己心中有数,这要是放在大清的话,应该算是军机大臣了吧!他笑道:“我怎么觉得这担子重得很呢?没这个噱头的时候,我还停自在的,这一捧在手心里,倒是觉得自己被捆起来了呢?”
“所有人都是这个感觉。”韩士承从杨立兆的桌子上顺走一根烟,“慢慢习惯就好!”
“我以为总统的位子会由王爷来坐!”浙江最近发生的事情在报纸上刊登了,韩士承他们也都看到了。
韩士承躺在杨立兆对面的椅子上,仰着脑袋,闭着眼睛说到:“我就知道会这样,当初王爷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不停地给我们画饼,今天的政治体系也是他参考大地另一面的那个强国所构建出来的。每次讲话的时候,他都像是在讲故事,但故事里从来都不包含他自己,他就像个局外人。我很好奇,大地另一面的那个国家是个什么样子,究竟强大到什么地步,也不知道我民国战舰有没有资格沿着他的海岸线走上一遭?”
天还没放亮,冷风刺骨,同是御门听政,唯独今天的气氛异常诡异,汪由敦跪在地上,认真地汇报自己在浙江的见闻。他不敢抬头,此时皇帝的脸必然是铁青的。一百多号人仅仅是在浙江废弃的衙门府里睡了一晚,便再无其他建树,真是丢尽了乾隆皇帝的脸,李星垣则闭着眼趴在地上,他真希望地上有条缝,能让自己钻进去。
“林子大了,什么鸟蛋都有,简直是无法无天!”张廷玉站在最前排,义愤填膺地数落严祌等人,“此等商贾贱民竟有不臣之心,想必是我大清的赋税低了些!”
“此与赋税无关?”鄂尔泰坦言,“西征准噶尔三年,耗费白银四千九百万两,其中大部分是从商贾身上抽的,这赋税可不低啊!你莫要胡诌,此事,依我之见,可能与赋税有一定的关联!”
“哼!你的意思是我大清苛捐众多,民怨四起,他们是被逼无奈,这才造反?”张廷玉立刻开始回呛鄂尔泰。
鄂尔泰不愿和张廷玉产生过多纠纷,一条疯狗,到处咬,你不能和他对咬,否则吃亏的还是你,他侧过身对着地上跪着的人询问:“你们确定造反的是商贾,而不是山匪流寇?”商人造反,可真稀奇,难不成真是赋税过重?就算这样,这造反也不应该出现在浙江啊!那块地方理应富庶,最富的地方造反,没有道理的!
“回大人!”汪由敦小声回答:“确实是一群商贾起的头,而且大部分都是富商,至于为什么会造反,下官也不是太清楚。”他只是不敢说得过于详细,一百多号人在睡梦里被人家一锅给端了,这是何等的丢人,大清的钦差岂是这般无用?
“那你可知道领头的人是谁?”鄂尔泰的提问很直接,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静静地等待答案,若答案是和亲王,那事情就大条了,若不是,那还好办,就当是大乘教般的贼子,直接派兵镇压即可。
汪由敦在脑海里仔细搜索,他既然回答得迟缓,那必然是个不认识的人,那也就不是和亲王了,养心殿里不少人松了口气。良久,他回答到:“好像叫严祌来着,字石介。但奇怪的是,他们造反却不自立为王,改为推举,严祌就是被选举出来的,不称王,换叫总统!”
当听到严祌这个名字时,弘晓心中咯噔了下,这个人他是认识的,一个学识渊博的秀才,只是怀才不遇,当初他在严祌的酒楼里赊了不少银子,若说带头造反的人是严祌,弘晓是不信的,但他没有说话,依旧站在后排耷拉着眼皮,静静地听着。
总统这个词来保没有听过,他说到:“即是造反,称呼便没有区别,可是,一群商贾是如何造得起反,手无寸铁,拿什么去反抗,日后又拿什么来抵抗大清八旗子弟兵?”
“非也!”阿里衮抬头道:“他们有火枪,有大船,船很大,非常的大,没有帆,没有桨,速度却很快,这种船绝不是大清的。他们定是勾结了洋人,听说,他们高价聘请了几个洋人,去学校当校长,真是闻所未闻,那蛮子连名字都起不好,竟叫什么‘白努力’、“呕了吐了”之类的,竟也敢来我大清教书。”
一听让洋人当校长,来保立刻炸毛,他怒道:“荒唐,我大清没有圣人之言了么?孔儒之道都是假的么?需要他们一群枯发碧眼的蛮夷来点化?真是岂有此理!”
“想来也就是一批乌合之众,受了蛮夷的妖言惑语,成不了气候的!”鄂尔泰毫不在意,“现在最要紧的是查清和亲王是否有参与其中!”
“微臣赞同鄂尔泰大人的话!”来保义正言辞地说到:“查明真相,也好还和亲王一个清白!”他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头就未必这么想了。
似乎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和亲王是否参与造反的问题上,而忽略了浙江谋逆的叛贼,阿里衮对着乾隆皇帝拜道:“启禀皇上,那群谋逆之徒不但嚣张跋扈,而且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微臣见过他们的火枪和战船,虽不见威力如何,但是使用武器的士兵微臣可是见过,无不是身材魁梧、孔武有力之辈,整个队伍的纪律性更是异常之高,实不可不防啊!”
与和亲王的问题相比,阿里衮所言声势实在过低,直接被在场的高官忽略了。
“你们可有见到和亲王?”问话的是来保,至于乾隆,自始至终都躺在龙椅上闭目养神,不是闲,是被气的。
汪由敦摇摇头,诚实地回答:“没有!从头到尾都未有见到和亲王。”
“这么说,此事与和亲王并无关联,只是单纯的一帮匪民造反罢了,是与不是?”来保对着卢焯问话,若是真和弘昼没什么关系,那么卢焯就是构陷,外加丢了官印,这便是罪加一等。
跪在地上的卢焯连忙抬起身,向着乾隆皇帝嚷到:“皇上!臣冤枉啊!此事真的是由和亲王一手挑起的啊!微臣所言句句属实啊!”说完便哭,哭完便是头抢地。
来保板着脸继续问到:“证据呢?没有证据,如何证明和亲王参与其中啊!”他很心急,不停地给卢焯施加压力。
久未发声的李星垣抬起头说到:“启禀皇上!现在当务之急并不是追究和亲王是否有参与其中,而是派兵南下,连同广东水师清缴叛党啊!”
“臣附议!”来保特别起劲,此时南下,亦有机会拉和亲王下水。
傅恒想要站出来,他是兵部尚书,由他领兵南下是最合适的,他左脚刚动,站前他边上的弘晓便拽住了他,并向他摇摇头。若是以前,傅恒一定会挣脱弘晓,绝不会和他站在一道线上,但今天他没有,弘晓拉了他,他便很老实地站在了原地。
一直坐在龙椅上聆听的乾隆极不情愿地睁开眼,字里行间带着火,“是天下太平久了么?是头驴就敢尥蹶子,金川完了,准噶尔来,现在准噶尔完了,浙江又来,是朕这个皇帝当的不随你们心意么?”这句话是咆哮出来的,乾隆额头青筋凸起,脸色潮红,一副吃人的模样。
一众官员统统伏地,不敢私言半语。
“阿桂,你即刻领兵南下,协同广东水师清剿叛党!”乾隆不再等待大臣商议,而是直接发号施令,他没有点名傅恒,他是知晓傅恒与弘昼的关系的,他真怕弘昼参与其中。
“那和亲王当如何处置?”说话的又是来保,不把弘昼扳倒,他来保便不死心。弘晓本是诧异为何来保总揪着弘昼不放,后又仔细一想,来保是站在太后那边的,便释然了。
“你们确定没有见到弘昼?”乾隆目光凌厉,如利刃刺在卢焯等人心头。
汪由敦看了看周围,李星垣又趴在地上不吱声了,他心中叹息,还得自己来说,“回皇上,确实未见到和亲王,按理,既然是造反,那自然图谋龙袍加身,若是和亲王参与其中,不自立为王,他又图什么?”
“哼!”卢焯冷哼一声,反驳道:“和亲王素来荒唐,他做事自然不能以常人之心去理解,汪大人此言岂不是在控告本官构陷之罪?”
汪由敦辩解道:“微臣只是就事论事!”他就知道,只要开口必定遭人怨。
“回皇上!”来保想了个策略,“之前因太后寿辰,而致宗室之会延期。皇上何不趁着宗宴之会唤和亲王进京?再者,裕太妃还在宫里,想来和亲王也不会不回来!”这是在弘昼没有参与叛乱情况下的一道双保险,万一平叛的过程中没能拉下弘昼,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把弘昼弄回京城,至于罪名,平叛结束后,多加个人,又有多难?
弘晓站在众人背后,他的眼光阴狠毒辣,侧首之时,正好对上鄂尔泰的眼睛,两人嘴角同时上扬,恰似狼狈之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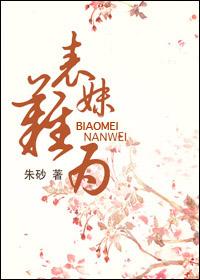
![[娱乐圈]闵其其想上位](/img/1067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