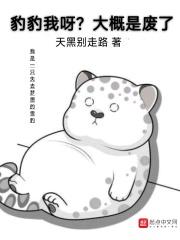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永日之崖写的什么 > 第17章(第1页)
第17章(第1页)
>
他的生活按部就班,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濒临失控的感觉了。
不过,他想,快结束了。
昨天夜里魏暮被他留在警察局外面的大街上,先不说那里距他所在的小区十多公里,按照他对以前的魏暮的了解,这人总是别人往后退一步他恨不得退三步,识相得不得了,就连之前两人分手一切也算得上干净利落,几年里魏暮从未联系过他一次。
这次纪随安不知道魏暮是因为什么转了性,真失忆还是假失忆,但在过去几天里他的态度没有丝毫软化,昨晚他又尽力心平气和地将话说得明白得不能再明白,如果魏暮身上还有一点旧日的影子,现在就应该已经离开,再也不会来打搅他了。
他这样轻松地想着,然而魏暮在夜色中独自站在梧桐树下的模样却蓦地闯入眼前,试图侵占他的思绪,纪随安蹙起眉,强逼着自己将那幅场景摒除出去。
他少有地没起床后立马出门上班,而是去了厨房,在家给自己做了一顿早餐,吃完饭后还颇有闲心地收拾了一番酒柜,这才去卧室换衣服。
他最近几年西装穿的多,大多时候都是整套上身,很少自己再去费心搭配,毕竟都是定制的衣服,任何一套穿他身上都极为熨帖俊朗,然而这天早晨他却看着衣柜里的几十套西装思考了两分钟,最终选了一套黑色带暗纹的,去掉原本那条暗红格纹的领带,换了一条宝蓝色的,又选择了同色系的宝石袖扣,甚至还替换了手腕上原本戴的表。
他闲适从容地做着这一切,这样微微带有强迫性质的高兴一直持续到他将车开出小区,看到路边长椅上坐着的魏暮才戛然而止。
清晨阳光笼罩着两侧街道,周围人来车往很是热闹,魏暮坐在其中,一身肮脏破败的衣裳,像是这世间唯一不和谐的色彩。
纪随安看不到他自己那一瞬间变得几乎要杀人的阴沉脸色,却能感受到从胸腔深处腾起、奔涌着将他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彻底包裹的狂怒与躁郁。没完没了了是吗?究竟想做什么?为什么?凭什么!他听到自己内心压抑扭曲的怒吼,恨不得立刻打开车门冲下去,亲自抓着魏暮的领子将他远远拖走,让他彻底地、再也不能出现。
这时,魏暮注意到了他的车,站起来朝他的方向走了两步,又像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脚一般停了下来,只是隔着一段距离静静地看着他。
纪随安用力地咬着牙根,他的手心被方向盘磨得生疼,几乎是用尽了所有的意志力才控制住自己,缓慢地踩下油门、转动方向盘,保持着最后的冷静离开。
纪随安的车转眼便融入了车流中,魏暮试图辨认,然而前方不远处就是一个十字路口,车辆多而复杂,不过片刻那辆黑车就彻底找不到了。虽然知道是徒劳,魏他却仍是站在原地忍不住看了许久,才又转身回到长椅上坐下。
他知道纪随安不愿意看见他,深夜走过来的一路上也想过是不是应该离开,然而每当这样的念头稍稍生起,心底便立马有个声音响起来,他如果走了,一切就真的彻底结束了,那个声音微小而虚弱,却始终不停地一遍遍向他恳求,说不要走,不能走,那是纪随安啊。
那明明是他的纪随安。
从小到大他习惯了退让,从未真正地争取过什么东西,生怕惹了别人厌烦,只有纪随安,就算拿刀一寸寸地扎进他的手掌心里,他也不舍得就这样放手。
没有钟表计时也没有事情可做,时间的流逝变得难以感知,而他的时间好像只剩了等待这一个功用。魏暮坐在长椅上一直没动地方,在这个位置,他能看见进出小区的每辆车,而在感应杆升起的短短间隙里,他有可能看到几眼纪随安。
渐渐地,头顶的太阳愈发灼烈起来,长椅边没有树荫遮挡,魏暮被晒得有些发晕,还有些想吐,他已经好几天没怎么吃饭了,胃里却始终沉甸甸的,没有一点饥饿的感觉。
身前有很多人走过,他怪异的模样招惹来不少打量的视线,魏暮的眼前却像是隔了一层无形的屏障,他什么都能看见,又什么都看不清,以至于身后的人一连喊了好几声,他才后知后觉地明白过来是在叫他。
他昨天进过的那家店的老太太正站在门口朝他招手,魏暮不知道她有什么事情,晃了晃脑袋减去些昏沉,他起身走了过去。
老太太手里仍旧拿着那件织了一半的毛衣,木制针织棒的一端翘在阳光里,显得十分温暖。她问魏暮:“我想挪一下角落里的那两个架子,但刚刚试了试,太沉了我搬不动,能不能麻烦你帮我一下?”
魏暮没说什么,点头答应后,照着老太太的要求将架子挪了位置,又帮她将上面原本放置着的东西重新摆好。做完之后,老太太连声向他道谢,说:“真是多亏了你,不然我一个人是怎么也搬不动的,这么一堆东西也够我摆上老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