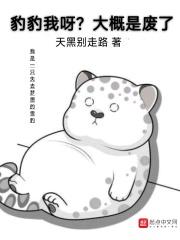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大驸马作者 蹬三轮飞的阿婆 > 第49(第1页)
第49(第1页)
寒酥就在帐门口,听见声音进去。温言让她挑出衣服,不给她去,她偏要去。温言穿上了一套整张羊皮毛做的袍子,脖前是翻领,胸前延至袍边,有多种颜色压边。只一串与压边同一色的项链,不再有其他首饰。腰间是皮质宽腰,挂着一柄小刀,脚上是玩弯钩靴。戴上一顶狼毛厚帽,两边垂下多股细辫子。温言踏出了帐子,外头已经是火把点亮,空气中弥漫着烤味。温言寻着声音走去,一路有对她陌生好奇的,也有认得她行礼的。突然,一把红樱银枪拦住她,温言转头看去,健黑英气郎跳下木桩,“美人儿,要不要和本将军去吃肉。”声音雌雄莫辨,温言一时吃不准。将士与兵是分开用膳的,这位小将军想请她去吃烤羊。童羡嗅着温言身上好闻的味道,像只猎犬一样不停嗅,“好啊。”温言同意,那人笑咧开嘴,“等本将军一会儿。”还真的只是等了一会儿,童羡回帐把银枪放好,洗了把脸就出来。“美人儿,你叫什么名字,没见过你。”“温言,来探亲。”“谁啊,本将军咋不知道谁有这么个漂亮媳妇。”“喏,那个帐子。”温言指了沈确的帐,搂在她肩上的手僵住,尴尬笑,“你叫什么名字。”“回大驸马,下官童羡。”中郎将童羡,放下手老实回答。温言在沈确嘴里听过她,知道了她性别,“童将军,带路吧。”“是。”当温言和童羡一起过来时,沈确黑了脸,有没有被占去便宜,这人男女通吃。被沈确那可怕目光瞪着,童羡挠了挠头,尬笑,掰开人立即坐下。被她挤到的人,骂她来的晚就坐边上去,童羡回他们拳脚。“你怎么和她一起来了,不是说不来?”“不来,怎么发现童将军这么有意思的人。”“她哪里有意思了,混账的很。”桀骜不驯冲锋将,说的就是她。空地四周有帐围起,顶空露天,中间有高高的篝火燃起。有伙兵在忙碌,手中刀不停。宋颜知道温言来了,她原本不想去,但不去,显得她怯。她打开了衣箱,身为世家,她自然与旁人也是不同的。在铜镜前试了好几件,不是嫌颜色太鲜艳就是太华丽,她翻找了许久,才找到一件合适的旧衣。无法和温室里的娇花比美,她突出自己的优势,身型高挑直挺。简单的一尾发,面上比军中女将都要白些细腻,她做到干净清爽,就出去了。宋颜来的晚了些,位置已经不多,但她在军中有好缘,不少人愿意空出位,和她挤一挤。她的视线,在温言身上停留了一会儿就收回,心想自己幸亏没有弄的明显。温言在这里,把他们衬得都像是山野人。来迟的宋颜,温言瞧见了,也瞧见了她的受欢迎,在一众女将中,她很突出,没有粗糙感,是非常英气的美将。温言拿着小刀在割肉,烤肉虽然闻着香,但她吃不惯,还是清煮肉能吃得下。烤脆的饼夹裹住肉片,再淋些酱汁,温言大口咬下,这边的羊肉一丁点膻腥都没有,真真鲜嫩。沈确原本在和人交谈,等他转过头来,见到温言自己安静在吃东西,没有一丝好奇色。
沈确在想自己是不是冷落她不高兴了,“羊肉还要吗,其他的要再来点吗?”温言抬眸瞅他,只大口嚼肉不说话,沈确不明白她怎么了,正巧有烤栗子送过来,知道温言会吃这个,沈确就是烫手也给她剥了起来。温言假惺惺说,“有点烫哎,两颗就够了。”“这里也没其他好吃的,没事,给你剥。”西北的毛栗子,个头特别大,得在上头划口子才能完整剥开。栗子很甜,温言看向沈确的眼眸也特别亮,沈确自己一个都没吃,全留给了她。细白的手指捻着栗肉,火光中柔毛冒下的脸,笑得温婉,散发着被疼爱的底气。宋颜把栗子握在手心中,捏碎开再剥,没有女子的精细吃法。她的目光,刻意的不去看温言。大胆踩船篝火上,有善乐器的将士弹弦拍鼓,有擅歌舞的将士脱去厚袍,露出结实身板和长腿。温言跟着节奏一起在拍手,演奏的乐曲是《战马嘶鸣》,快节奏的战舞,温言的身体也在晃动。领头的人看着她,露出白牙笑邀请她一起。温言脱下帽子和厚袍,应邀过去了。她曾不学无术,但十分善骑与舞,温言上场引来了许多响亮哨声。温言和领舞的那人对跳,她下盘稳健,双臂身体柔韧,女子的美柔与男子的刚硬形成了视觉对比。舞者不止身态,还需要眼神,温言盯着季应祈,脸上笑意不多。季应祈前倾来轻撞,温言转身躲开,脚踢他后膝盖,抢了他领舞位置。温言的动作越发舒展,甩裙旋转跳,高扬起裙摆,一股子潇洒自由。就在此时,季应祈打了个手势,乐曲变换,不再是激烈战鸣,而是轻松明快。他领着一群人以夸张慢舞步走向温言,温言双手抱臂,偏头不理。季应祈要再上前,温言一手推,他夸张往后倒去,后头一群人也往后倒。等沈确带人巡视结束回来,听到了掌声欢哨声,视线没瞧见温言,还在疑惑她哪里去了。突然,看到了她被围在篝火中间,被一把抱起坐到了季应祈的肩上,季应祈固住她的腿左右摇晃,周边人都在吹哨起哄。温言骂季应祈流氓,他是温言打马球朋友中季崇礼的大哥,都认识。季应祈充耳不闻,载着她摇来摇去,鬼知道他多久没见过正常女人了。得接触一下,免得自己变态了。温言宛如众星捧月,坐在季应祈的高肩上,是人群中最显眼的人。温言被颠的胸前两兔子弹跳,双手抱着他脑袋骂不停,季应祈隔着衣料拿脑袋顶她胸口,玩得不亦乐乎。被占便宜的温言,气得开始双手掰他的嘴。温言被扔进了沈确的怀里,季应祈揉着自己的嘴,“温言,几年不见,你还是这么无赖。”被倒打一耙,温言从沈确怀里起身,拿桌上的栗子壳扔他,“臭流氓,臭流氓。”季应祈大笑着跑开了,徒留温言不停摇着沈确,要去揍他,沈确应下,站起来,脱了外衣,找他去摔跤。沈确和季应祈是好友,是能将背后交给对方的人。除了载歌载舞,精力充沛的军中人还在玩摔跤,童羡在叫嚣着下一个,周遭跃跃欲试的人有很多,很快就有人应战。温言不在帐中的这段时间,寒酥是自由的,虽然她心中有玉尘,可真的架不住军中有许多人向她示好。温言提醒她不要收太多人的东西,免得应付不过来,但寒酥还想再挑一挑。她把自己打扮了一番,分别和三人吃了三顿年夜饭,时间安排的妥妥。正当她开心要回到自己帐中时,一个人拦住了她。因为军中没有其他侍女,寒酥是独自一人住,没有灯火亮起,黑暗中寒酥被捂住了嘴巴,心中后大悔。娇嫩肌肤被乱啃,身下被按紧,寒酥痛与快并着。既然如此,她心想着那就选他好了,第一个吃饭的人。边境长大的大男孩,抱着寒酥亲了又亲,才不舍离开。他长得不错,又热情,寒酥觉得自己选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