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楠文学网>亲爱的送给我玫瑰花 > 第13章(第1页)
第13章(第1页)
>
袁秩舒又问:“当年为什么动手还记得吗?”
王奈的眼神有些发直,他似乎在回想十五年前案发时的场景,停顿了很久才摇摇头:“不记得了,就记得我们……我们好像吵架了,因为什么吵的不记得了。我很生气,就失去理智了。”
“然后你就拿刀砍了她?”
“对。”王奈答,“砍了。”
“那你看到你的女朋友倒在血泊中,你想的为什么不是看看有没有救呢?而是说去采取那种极端的手段?”
“不记得了。”又是不记得了。
王奈低下了头,似乎那段回忆对他来说很痛苦。
但潘望秋知道不是这样的,恶人痛苦的永远不会是他所犯下的恶行,他们痛苦的只会是作恶后即将受到的惩罚。
就好像对方连杀人动机都不记得了,不记得自己是如何犯错的人怎么会忏悔呢?就算忏悔了,那也一定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带着博同情、期望减罪的目的。
作为校园暴力的受害者,潘望秋太了解了——伤痛永远只有受害者记得,加害者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这是一条快讯而非专访,采访到这里就够用了。
袁秩舒朝着举话筒的民警点点头,真诚地道了谢。
电视台的一行人又同民警客套了几句就打道回府了,双方是老搭档了,每次有案件需要采访都是这样的。
回到台里,袁秩舒交代潘望秋将早上的素材上传并听同期声,听完后把整理好的文档传到她专属的文件夹中。
在电视台里,每一位正式员工都有自己专属的、公开的文件夹,里面存储着自己做过所有新闻的素材。
记者储存的是文稿,主持储存的是音频;而同一条新闻的摄像和剪辑往往是同一个人,他们的专属文档中储存的则是拍下的视频素材。
而同期声顾名思义,就是将采访内容打成文字,一般由记者本人自己敲。但这只是潘望秋上班第一天,自然不可能让他独立完成新闻报道,只能做这些边角的小活儿。
潘望秋接过摄像交给他的相机储存卡,同一起出任务的两人说再见。
摄像早上的工作到这里就算完成了,归还仪器后就可以打卡下班了。
等潘望秋将同期声敲出来,袁秩舒再根据同期声撰写新闻稿,而后新闻稿将交给审核。审核未过则必须对稿件进行修改,过稿则将稿件传给主持人录制旁白。
到下午三四点,主持人负责的旁白已经基本录制完毕,这时摄影兼剪辑再来上班。他们根据记者撰写的文稿配以画面,将那些内容剪成一条连贯视频,一条新闻就这么产生了。
潘望秋将早上拍摄的素材导入云盘中,刚戴上耳机没打多少字,就听到逐渐靠近的脚步声。
这间机房有两排电脑,粗略一看有八到十台,目前机房里只有三四个人。
推门而入的是一位中年男人,他径直走向潘望秋的座位,屈起手指敲了敲潘望秋的桌子。
潘望秋摘下耳机。
他面前的男人脸上不带半点笑意,语气也没有半分商量的意思,傲慢地对潘望秋说:“这是我经常用的电脑,你到其他地方去。”
潘望秋一时没反应过来,下意识地站了起来,谦卑地表态:“这就给您用。”
那个男人没有道一句谢,瞥了诚惶诚恐的潘望秋一眼就坐了下去,仿佛潘望秋将电脑让给他是理所应当的事。
等潘望秋在新电脑面前坐好时,他的脑子才恢复转动,他进来时机房中不止坐着一个人,他们本可以提醒他这台电脑有一个霸道的使用者,但他们没有,是想看新人出糗当做饭后笑料么?
再说,他刚才是有拒绝权力的,也理应拒绝,两个人都在工作,没有谁比谁高贵;更何况他工作一半更换电脑未免会有诸多不便,对方不会不清楚,这是在明目张胆地欺压新人。
因为初中时遭受的校园暴力,潘望秋的反应会比常人迟钝些,下意识的反应也只会忍让与道歉;这或许是他的大脑潜意识对他的保护——不要那么敏感、迟钝些、再退一步就能少受点伤害。
耳边敲击键盘的声音不绝于耳,潘望秋也没有找对方理论的勇气,只能默默忍下这件事。
他听完同期声不过中午十一点半,他摘下耳机,才发现和他一起在机房工作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
他将文档上传到电视台的数据库中,打开了微信给袁秩舒发去一条消息:袁记,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袁秩舒很快回了消息:没有了,谢谢你。
就在潘望秋打算将手机收起来时,又一条消息弹了出来。
卫恕:中午几点下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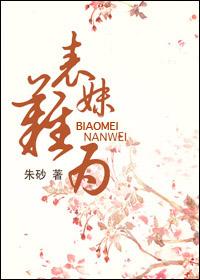
![[娱乐圈]闵其其想上位](/img/1067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