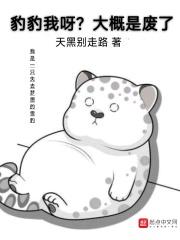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太子殿下今天又在装瞎吗笔趣阁 > 第85章(第2页)
第85章(第2页)
婉柔从没见过男人如此柔情似水,她自问这事由自己来做,也绝做不到这般轻缓细致。
她更没有把握,进屋做这么多事,还不把赵煜吵醒。
只得自愧不如。
烛火暗淡,窗上的投影跟着暗下来,看不见了。
只是好久,都不见太子殿下出来。
婉柔心里也说不清是何感触,飞身自树上一跃而下,回别苑去了。
再说赵煜,他看着卷宗内参,细想当年案件的始末,很多地方都说不通……
更甚,可以说是莫名其妙。
他本来仰在卧榻上捋思绪。
无奈内伤初愈,精气神不比全盛之时,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困意袭来,眼皮重得像铅铸的,身子半分都不愿再挪动,便就这样睡了。
再醒来时,天边已经擦了白,自己万分难得的,连姿势都没变过。
坐起来,才发现身上盖着件衣裳,只一看,便知道是谁的。
赶忙环顾,可屋里除了自己再无旁人。
沈澈不知何时离开的。
他把衣裳叠好,好好放在卧榻上,走到窗前,把窗子重新推开,让清晨的空气溜进屋子,灌入肺里。
翟瑞,冤狱坐了近二十年,当年的证人证物,大都不复存在。
能给他翻案吗?
赵煜也没有把握。
但他愿意一试。
看看天色,他叫来衡辛,让他去刑部内牢,把翟瑞带过来。
衡辛二话没说,难得毫不多嘴,应了一声,便要去办差。
“哎——”赵煜鬼使神差的开口道,“他……太子殿下呢?”
衡辛又低着头转回来,躬身答道:“小人不敢打探殿下行踪,但猜想,此时许是还在安寝。”
是了,此时已是初夏,天色虽然微明,但时辰,其实早得很。
赵煜摆手,让衡辛去提人。
衡辛转身的瞬间,他恍惚看见这小子脸上露出丝不老实的笑意,笑得奸猾。
赵煜摇摇头,觉得是自己看错了。
他只知道沈澈在他睡着时,前来找他,还贴心的给他盖衣关窗,可他不知道,那人离开时正好与衡辛撞上,就在半个时辰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