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楠文学网>君子无罪怀璧其罪意思 > 第92章(第1页)
第92章(第1页)
>
一则是寄居耿府的颜老夫人病故,因为耿府如今声名狼藉,耿家人又接连暴毙,竟是连一场像样的丧事都办不成,二则是问刀楼虎兰刀尊木梓横尸荒郊,尹枭来告知时萧珏便知不好,但当日即便斥责于他,那人也只答一句,‘殿下只教我盯着朱兄一举一动,这二人虽身死但朱兄并无何举动,是而便暂且扣下了。’
萧珏清楚这二人都与朱怀璧关系匪浅,一个是不能相认的生身母亲,一个是同甘共苦、亲如手足的义弟,朱怀璧素来能忍,虽当时没有何举动,但心中必已是滔天怒火了。但即便是他日夜不休赶路,也尚需十来日才能到崇阳,为了赶这一路竟不知跑死了多少匹马。
“王爷莫急,尹某这不就给您带信来了……!”尹枭前脚迈进府衙正堂,后脚一杯热茶就砸在了脚边,“诶~王爷别心急啊!凉州知府是赴宴去了,王爷现在去或许还能有所助益。”
“何人的宴?”
“绥南王…杨羡宇。这名讳,王爷该是熟悉,不过说是赴宴,不如说是被喊过去的。”尹枭缓缓说出一人,并不避讳堂下的官员,可见绥南王请知府大人‘赴宴’并不是稀罕事。至于这绥南王萧珏确实知道,但更多的是认识他身边的侍卫。当日借由朱怀璧之口,他才知晓绥南王身边的侍卫竟是当年拼死护住他兄妹的岑溪之兄。
然而萧珏对此人说不上有什么好感,毕竟季南珩曾在无意之中提及绥南王说了很多朱怀璧以色侍人的闲话。
尹枭又道:“绥南王是抚宁长公主的儿子,掌管淮南州郡多年,比起凉州府的屯兵,他若是肯出手,只他身边的岑侍卫便足够震慑江湖众人了。”
萧珏未答,只是横眉瞪了他一眼道:“知道了还不带路?!”
“府衙外备了马,王爷请。”尹枭倒不在意,微微一笑侧身让路。他做事也同样走一步看三步,但不同于朱怀璧,萧珏对此人却是亲近不起来。
也不知是偶然还是故意,绥南王设宴的地方便是在崇阳城。杨羡宇此人行事张扬,素来不会遮遮掩掩,果真就包下一整座酒楼等着萧珏。与其说是设宴请凉州知府来,不如说是刻意将此人唤来,等着萧珏上钩,毕竟以这人身份,各州郡刺史都是上赶着巴结,一个小小的知府又有何脸面让他宴请。
时而见到那凉州府知府满头大汗站候在一旁时,萧珏并不意外。
杨羡宇其人,他是头次见。瞧着并不显老,一身织金翠羽的华服绣着青色的鸾鸟,白面并未留髯倒像个风流文士,但萧珏知道此人纵横淮南绝非只是仗着抚宁长公主名号的二世祖,是而开口十分慎重,毕竟名义上,绥南王也算是他表叔。
“表叔在此设宴,缘何不叫侄儿一声。”
“原是听说城外好戏开锣,怕侄儿错过,特意摆上一宴请你一道去看。”杨羡宇俨然一副将萧珏算计进去的模样,似乎是笃定了他会为了朱怀璧赶来,更会去凉州府衙借兵一样。
萧珏侧头看了眼抱臂靠在一旁的尹枭,似是有所怀疑,转回头来道:“表叔好意,侄儿心领。只唯恐辜负表叔这份好意,便先领了人告辞。”
言下之意便是拒绝。
杨羡宇也不多与他兜圈子,萧珏刚起身要带那知府走,便听得身后人悠悠说道:“你信不信,没有本王的命令,他一步不敢出这酒楼,更不会为你动兵?”
绥南王与永昌郡王同是郡王爵,但前者手握大权,为州郡上下官员争相巴结之人,后者却只剩下空头爵位和家财,杨羡宇能说出这般命令,足可见绥南王在淮南势大。
萧珏并未与杨羡宇置气,他反倒看向尹枭,冷声质问道:“尹阁主本事不小,连表叔都被你笼络住了。”
这话说得十分肯定,尹枭只是笑笑拘了一礼道:“尹某只是未王爷找个有力的帮手,毕竟您日后的路不是朱怀璧一介布衣能帮的。”再者绥南王对朱怀璧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执着也是尹枭意料之外的,但对于大业而言,多一个绥南王他也多一重保证。假使日后隋晋留手抑或是朱怀璧不想死,他还有绥南王这步棋可以走。
当然这等会戳萧珏肺管子的话,他并没有如实告知,然而当萧珏察觉到他与绥南王有所勾连时,男人反倒心满意足地笑了。
“也罢,侄儿这性子与庆嗣表兄年少时有些相像。”杨羡宇说的正是萧珏的生父,先永穆太子萧庆嗣,他说罢跟着起身,“本王也不要侄儿记得什么恩惠,便当时报答当年表兄撮合之情罢了。只是侄儿若是有所感念,便让本王再见一见你师父,我与他也有十五六年未见了,思念得紧。”
此刻不知江湖情势,萧珏自知耽误不得,杨羡宇扣着凉州知府,只怕他再去找旁人亦是无用。再则凉州刺史匡汶荆是萧庆祯的人,他若是求到这人头上,只怕是日后留下把柄给萧庆祯,更是用不得,而绥南王势大,即便是太子也不能轻易撼动,他借对方之势确实是眼下最有利的选择。
是而萧珏并未阻拦。
有绥南王的私兵跟着,萧珏更不需顾忌那许多,带上苏招并一众侍卫快马直奔奉剑山庄,至于绥南王和凉州府知府则坐着车驾走在后面。
数月前来时,这奉剑山庄还是一副鼎盛之势,如今再来竟已显颓败之势,而门前显然已经过一场恶战,自山庄门口一路走来,四处竟死了不少人,细看之下全都是耿府剑侍打扮。
这场跨越二十七年的恩怨孽债源起奉剑山庄,自是要在这里终了。萧珏之前曾细细读了尹枭送来的卷宗,方知闻人家当年祸事,在知晓朱怀璧便是闻人瑜之后,竟发觉朱怀璧同当年的自己一样,父母亲长被害,孤身一身流落江湖,只是自己当时得朱怀璧庇佑十年,然而当年的闻人瑜却是无处喊冤、无人可求。
从闻人瑜到朱怀璧,这其中经历了什么,只有卷宗之上三两词句一言带过。
萧珏未经历过,但思及自己若是一朝龙游浅滩,不得不向旁人卑躬屈膝,可能撑过三十年?
也不知是谁眼尖瞧到,喊了一句,“官兵来了!”
“这不是……季少侠?!他不是被逐出……”、“他为何会和官兵一道?”
原本聚在堂前的江湖人纷纷转头,十分谨慎地看向来人,有人认出了萧珏身份,正是被朱怀璧逐出门墙的季玉朗。
“师尊,我回来了。”萧珏却不理旁人闲话,径自朝正中那人走去。
“……”朱怀璧一身红衣之上染了不少血,手提赤婴刀,眼神凌厉,却并不应萧珏的话,他脚下踩着一具尸首,却是沈琦。
萧珏站在他身边,一齐看向捂着肩头面容狼狈的老者,耿青梧陪在老夫身边,父子俩今被困死在这里孤立无援,而他们身后,还有一个蓬头垢面疯疯癫癫的老者。
这些日子先是宁、常两家接连出事,影门寻仇更是牵连出耿垣当年满身血债。耿家声誉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一个疯了的宁裕龙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当年三家围杀闻人家,并把常俞白同前影门护法暗通款曲,并诛杀正道之士的罪责通通安在已死的闻人正身上等一干丑事通通说了出来,才教人知道了当年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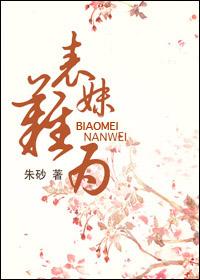
![[娱乐圈]闵其其想上位](/img/1067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