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楠文学网>天娇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 第15章(第1页)
第15章(第1页)
>
这才是门阀士族的立身之本。
身逢乱世,空有满腹才华,却无护身之双拳,也只能落得一副可怜的面貌。
她可以将自己的后背露给陆绰与陆长英,长宁可以完全信任真宁大长公主,在这世上陆绰能够信任与托付的人,胞弟陆纷一定能算一个。
毕竟一母同胞,一脉相承,血脉相连,照陆绰的话说,“人,始终都是会背叛的,若筹码够高,连周管事都有可能倒戈相向。可阿纷不会,没有人出得起价码买得动血脉。”
士家为何历经数朝亦屹立不倒,因为他们都分得很明白,敌人是谁,自家人是谁。
长亭停了停手上的九连环,老宅有隔房的叔伯经营,一直有条不紊,二叔陆纷就算一时上不了手,也自有人指教,不需要胞兄千里迢迢遥祭信件以作指正的。
既然并非指正教导,那是什么?
父亲,到底要做了什么?
“审时度势。”陆长英轻声提醒。
内厢熏着百叶香,是陆长英惯用的,气味清甜,很淡却愈久弥新,长亭沉下心来,手上下意识地转动九连环,古玉撞在古玉上,发出铃铃钝响。
“我们日前所处的局势……石家……”长亭轻喃。
石家愿意耍手段让陆家不得不留下来,那其他人家呢?其他人,其他更莽更粗的人,会不会手段都不乐意耍,直接拿硬家伙在陆家这块肥肉上狠狠咬上一口呢!?
平日里若一辆马车的横辕上写了“陆”字儿,庶民寒门纷纷避之不及,谁还敢贸然靠过来……
偏偏大乱初起,人的心思也活泛起来。
这怕也是陆绰最初未曾想到的。
时不予我……
长亭无端端地想起这四个字儿。
“有一个石家,就有张家、王家……父亲不敢拿全家的安危涉险,从建康北迁,本是为了避险,哪知这一路便是险境……”长亭语声清浅,抬头看向陆长英带了些不确定,道,“父亲是怕那一千家将撑不了台面?索性放开手脚,敲山震虎?”
与其遭不知轻重的人惦记,不如率先亮出剑来,是震慑也是自保。
所以写信告诉陆纷,是再遣兵将来也好,是沿路放哨示威也罢,多一重保障,多一分安心,谁也不会拿家眷的安危去冒险。
陆长英渐渐坐起身来,目光清明看向幼妹,慢慢笑起来。
黄昏鸦雀,驿站地处弈城东北部,远离热闹喧哗中心,长亭换过藏青缎边暗纹长襟,着暗绸身披大氅,陈妪坚持要让小姑娘戴上帷帽,“北地民风彪悍,您的身份与那些个人家不一样!”
是在暗指那日石家姑娘石宣吧?
长亭暗叹一声,这天下局势都要被打乱了,谁又与谁不同啊。
到底拗不过陈妪,戴上帷帽,眼前深青纱幔罩住了整个眼界,朦朦胧胧地透过间隙,与长宁上了马车。
符氏一辆马车,两个小姑娘一辆,换成了十足内敛的榆木黑漆马车,陆绰、长英与长茂驾马前行,往东市集去。
小长宁兴奋极了,一上车便歪在长亭身边的软枕上,笑道,“现在一上马车便晕晕乎乎的!难受得紧!”
晌午与长英的那一席谈话让长亭心里沉沉的,笑不出来,什么时候陆家也需要顾忌旁人了……
小长宁自然没有办法明白,靠在车厢边,偷偷撩开车帘向外看,市集已然慢慢亮起灯火来,长亭眼风一瞥,弈城的晚市集灯火通明,亮如白昼,外间的吆喝声,嬉闹声此起彼伏,热闹得十分市井,却让人无端亲近。
长亭没由来地叹了一叹。
石猛出身草莽低贱,无名儒大家教导,亦无古籍孤本读阅,他丛哪里学来的这些治世之道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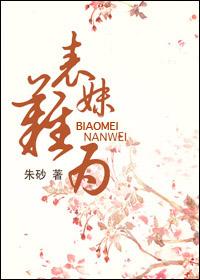
![[娱乐圈]闵其其想上位](/img/1067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