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楠文学网>盐店街简介 > 第70章(第1页)
第70章(第1页)
>
“对不起,”他终于在她耳边说道,“是我害怕……。”
她用洁白的手捂住了他的嘴:“不,不要说出来,不要说……。”
她把脸紧紧贴在他的肩上,其实她想说,她比他更害怕。至于怕什么,她却暂时想不起来也不愿意去想。
墙壁上透着淡淡的日光,两人紧紧相拥,那影子投在金黄的光晕中显得梦幻而孤独。静渊看着那团模糊的影子,多像小时候自己在布满晨光的书桌上练字,故意把毛笔蘸了墨扔进小水缸里,那清水中腾起的一团墨云。他是多么讨厌写字啊,可父亲和母亲总是逼着他写,请了多少师傅,他赶走一个,又请来一个,他掰断一只笔,紧接着就又给他买十支笔。
“你掰呀你要都把它们掰断了,我就不让你再练字了。”母亲冷冷地看着七岁的他。
他倔强地把手伸向那些毛笔。
母亲却把那十支笔捆成了一团扔给他:“掰吧。”
他掰不断,他怎么掰得断呢
他写得一手好字。写字的时候,终于把自己还给了天与地,做一个顶顶端正听话的小孩。
人们都知道盐店街的林少爷一手字峻于古人,如龙蛇战斗,如青云微笼,几旋雷激,操举若神。可是谁也不知道,他有多么厌恶自己手中的笔,笔下的字,他有多么厌恶自己。
静渊抱着七七,让自己的吻如潮水般淹没她,也淹没他。
他怕这潮水退去,因为潮水总是退得那么快,白浪滔滔,岁月荒荒,所有的杀伐、安宁、爱恨,总是一片狼藉。
现在若给他十支毛笔,他一定能掰断。可是如今,他想掰断的不是笔,是他自己。
……………………
茶杯,青花茶杯,印有蓝色螭纹,被摔碎在地上,茶水溅了一地。
罗飞跪在地上,眼神坚毅,面无表情,胭脂站在他身旁,低着头,双手紧张地绞着一张粉色手绢。
“带着这个女人给我滚出去”秉忠脸上如罩严霜,“我让你去扬州是去做生意,不是让你去嫖女人”
胭脂身体一颤,脸色顿时变得苍白。
“爹,”三妹在一旁看着不忍,劝道:“你怎么不听哥解释就发火。”
“爹,”罗飞声音冷静,“胭脂是个好女人,这段时间,她一直在照顾我。我知道你嫌她出身不好,可是她跟我的时候,是清清白白的人。我答应了她,要照顾她一辈子。”
罗母站在秉忠身旁,一脸痛心疾首:“阿飞啊,你爹为了你,下了多少心血,这一辈子的钱全投在你身上了,为的是什么?就是要让你出人头地,要你以后在清河,不会被人说是佣人的儿子看不起你你说要去扬州,你爹便安排你去扬州;你说要开运盐号,你爹便帮你在成都找关系、在江津给你开铺子,我们知道你爱慕七小姐,七小姐嫁了人,你伤心,你难过,我们以后自然会给你找个好人家的小姐,可你不能破罐子破摔,找来这么个烟视媚行的风尘女子啊”
胭脂咬着嘴唇,两行眼泪默默掉了下来,一滴泪掉在罗飞的衣袖上。
秉忠看了,丝毫不为所动,见儿子仍是一脸倔强,心中怒气更胜,重重的哼了一声。
罗飞道:“胭脂,来,给爹跪下,”伸手将胭脂往下一拽,胭脂流着泪跪在他身旁,罗飞道:“如今你也看到了,我家容不下你,但你要做我的女人,我不能不给我父母一个交代,你若承我的情,便在这儿给我爹娘磕个头,他们认你也罢,不认你也罢,你磕了头,就算是尽了道义。我既然认了你,便自会好好跟你过日子,不会再让你受委屈。”
胭脂听了,擦了擦眼泪,默默朝秉忠夫妻磕下头去。
罗母长长叹了口气,秉忠直气得浑身发抖。
罗飞抬起眼来,看着父亲:“父亲,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儿子的苦衷。”
也不待秉忠回答,径自起了身来,将胭脂扶了起来,两人一同出了家门。三妹看看父亲母亲,再看看哥哥,顿了顿脚,追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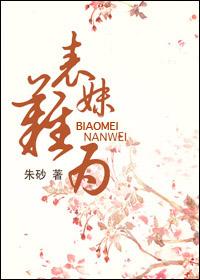
![[娱乐圈]闵其其想上位](/img/1067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