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楠文学网>西风txt > 第5章(第1页)
第5章(第1页)
>
他看见床上的男人喉头滚动:“这,未免太过分了。”声音因情欲或饥饿低哑粗糙。克莱蒙用小刀切开石榴,掰开一半拿上床,说:“你募集一支队伍,给了每个人他们需要的,为声名狼藉者恢复名誉,为家人失散者找回亲爱的人,让他们替你卖命。除了我,既然你不能掌控我,为什么要找上我?”
你暴露了你安全感的缺失,克莱蒙听见心中的警报声:为什么总是克制不住对这个男人袒露那样多情绪?然而他听见亨利说:“因为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就非常喜欢你,那种感情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所以你一定要在我的队伍里。”
克莱蒙愣住了,像是一件没想过能得到的珍宝,从天而降,那种惊愕变成脸红的羞恼。尤其是亨利抖动手腕,手铐撞击,说:“你一直盯着我看,你知道我的尺寸,你想要它。现在,解开手铐,我们可以尽快干正事。”
克莱蒙却狠狠咬上他的颈侧,犬齿刺入皮肤,灰白色头发,强壮赤裸的男人低叫皱眉。克莱蒙紧压他的肩膀,从牙缝里说:“没错,我是想被这条东西操。但是你是真的不知道你可以有多可恶,在面对你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我只想把你的脑浆操出来。”
亨利却抬起一边眉毛,故作讶然地说:“那你还在等什么?”
克莱蒙的手指陷进石榴粒里,一只手分开亨利的大腿,那个强壮的男人主动打开大腿方便他的手。刚运动完的身体温热紧绷,覆盖在一层薄汗下。克莱蒙用大量润滑剂,薰衣草味的,毫不怜惜地插入那个地方。
他长而有力的手指伸了进去,指甲并不长,手上虽然无可避免地有茧,却干净灵巧,所谓的“樱桃采摘者”,可以伸进每个男女的性器里搅动,玩弄快感的核心。
他找到前列腺的位置,准确长久地按压。那具强健的身体毫不掩饰自然的颤抖,下腹抽紧,光是看着他克莱蒙就硬得快要射了。他一边用手指玩弄这个男人,一边用阴茎顶着柔软的会阴磨动,把亨利下身的毛发弄乱。然后始料未及,那个老男人居然主动抬起下身蹭动克莱蒙的阴茎,又侧头含住他的手指,露出一种猎食者的笑容,用牙齿轻咬,吞入指节吸吮手指上石榴的汁液。
克莱蒙脑海里一片空白,居然因此射精。他狠狠掐住亨利的脖子,眼睛都红了,却听见亨利沙哑戏谑地说:“如果你不介意,快做完这些事,我期待尽可能早地吃到午餐。”
他是故意的,恼怒之后克莱蒙立刻冷静下来,老一套的虚张声势,扑克玩家的常态。他用一种故作优雅地语气说:“如果这是你的愿望。鉴于你让我现在无法插入,恕我失礼,我大概只能一边吃午餐一边看着你了。”
他从脱下的长裤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玩具,塞进亨利的屁股里,推到正抵住前列腺的地方,之后洗手,一个人坐在餐车边享用午餐,不时调动手边的遥控装置。在喝汤时就把功率开到最大,不久他就听见了那个男人压抑的喘息声。
克莱蒙很快感觉到阴茎再一次充血,并且仿佛在弥补上一次没能操进那个男人的屁股,这一次状态更贲张。年龄让他享有优势。亨利很快放弃了压抑,卧室里都是他低沉的声音,像是来自色情热线。
克莱蒙吃下除甜点在外的许多东西,他需要体力。亨利明显知道什么能让他失控,他用那种尽力镇定,却沙哑粗糙的语调说:“把它拿出来,可以吗?……‘请’你操我。”
后来的发展按克莱蒙的预料。他们的做爱从不是一场单方面的攻克,而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当意识到他不被允许去用手抚慰自己,只能被操到高潮,亨利居然开始指导克莱蒙,重一些,对我粗暴,就是这里,按住我的胯部……在此之前他没有被人操过,但是适应能力如此惊人。他太了解他的身体。
克莱蒙发誓他很快会后悔教会自己,因为一次两次高潮并不能让克莱蒙放过他。阴茎高潮有不应期,但前列腺高潮没有。第三次高潮,他被操到大量前列腺液混合一点精液流出,阴茎被这些东西包裹,之后就再也没有精液了,只能不停干性高潮,透明的前列腺液像失禁一样滴出。
他一定有些晕眩,克莱蒙浅浅埋在他体内,听他发出的喉音。至少有两次,他是被手指或是玩具干到高潮。但克莱蒙在他身上也耗费了近乎所有体力,他不打算真的把亨利锁上几天,尤其是在他说爱他以后。克莱蒙抬背吻他的脸颊,然后伸手到床边的餐车上端走甜品。
甜品是堆成小山的奶油泡芙,按他的嘱咐,酱汁分开放。他转动手腕倒出,用亨利宽阔的胸膛盛放甜品,亨利发出一声低喘,然后巧克力混合朗姆酒的浓汁倒在奶油和小泡芙上。
克莱蒙弓起背舔舐他被巧克力酱覆盖的乳头,那里的皮肤已经红肿,舌头灵活地围绕着乳头打圈,他的阴茎还插在亨利身体里,随舔舐的动作小范围顶动,几乎可以算温柔。
亨利仰头说:“你用食物来做这些事。”
“这是对一个厨师最好的赞美——把他的作品摆在我爱的人身上。”亨利因为那句迟疑的“爱”促狭地笑起来,却在能说话以前,被克莱蒙叼起半个泡芙堵住了嘴。
年轻的男人居高临下地说:“那你又是什么?用身体换取食物的男妓吗?”
“我可以是你的男妓。”亨利用那种低沉醇厚的声音说:“不过操一个在我的年纪的男妓,你确定你没有恋父情结?”
“因为你不是收费高的那一种,更像生活所迫走上街头的那种。”年轻的男人被他的声音和自己的幻想再度点燃欲火,抬起那个男人强壮的腿,腰胯与他撞击,狠狠侵犯他:“告诉我,你是不是曾经在军队里。”
克莱蒙一直猜测他也曾是陆军的一员,像他过往听过的流言,有少数人十分出色,然后有一天起被调职,然后仿佛凭空消失了。多数人认定他们去了兰里,做一份必须有人做却见不得光的差事,间谍,特工,或是随便什么你愿意称呼的头衔。
他不知道亨利这个名字是否真实,不知道他的过往,不知道他的家乡,甚至年龄也只知道一个大概。因为,亨利说:“你太聪明了,给你拼图的一块你就会尝试拼出全部。”
但现在,就像只是为了满足他的性癖,为了床上的性癖,亨利纵容地说:“我确实曾在陆军里……然后被开除。”他的声音中甚至带着低沉苦涩,那种一事无成的老男人对痛苦的瑟缩。克莱蒙呼出的气都像燃烧的烟,他把亨利操进床垫里,心里有些什么在尖锐的痛,但又有什么在兴奋咆哮,明知道亨利的话不可信,却受到安抚,他不再是一个背弃了姓名和过往的骗子,而如同回到许多年前,他是那个年轻的阳光下的中尉,穿着便装在军事基地外的酒吧游荡,忽然有了性趣操一个年纪大的男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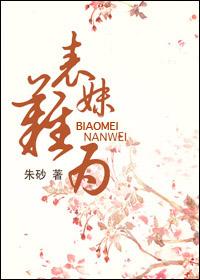
![[娱乐圈]闵其其想上位](/img/1067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