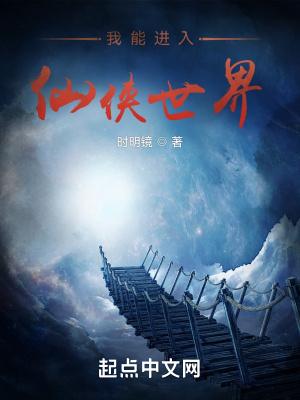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入骨相思知不知上一句 > 第83章(第2页)
第83章(第2页)
微浓的鼻息声传进耳中,姜漓定定地睁开眼,见裴玄思阖着双眸,呼吸调匀,就跟当初小时候听着无聊一样,竟然已经睡着了。
她抬手替他撩着额前散碎的发,垂眼静静地凝望膝头上安然入眠的俊美脸庞,神色漠漠,怔怔出神。
夜色冥冥。
院子里忙活的声息还未停歇,外面厅里的火光顺着棉布帘子的缝隙进来,隐隐还能嗅到纸钱烧化的烟灰味儿。
只有里面这间内室是静的。
灯已经全熄了,窗外的夜光和帘缝间溢出的光交织在一起,又漫散在这片黑暗中,杳无踪影。
杳寂中,几声磕响混杂在朔风卷动枝杈的窸窣声里,既隐秘又凸显无疑。
纱帐内貌似沉睡正酣的裴玄思轻挑了下唇角,双眸立时睁开,没有一丝怔迟,也不见意态朦胧,手上轻快地揭被撩帐起身。
但下榻之后,他的动作便稍缓下来,拖着那条受伤的腿,走向窗口。
外面的磕响一阵接一阵地传来,愈来愈显得急切,但每次都只有三声,简单而清晰。
裴玄思不急不躁,仍旧僵直地挪着那条腿向前挪,半晌才用这种怪模怪样的方式走到窗前,伸指提起销子,扯下塞缝的棉布,推开两扇不大的木牖。
寒风猝然涌进来,立时吹得衣衫鼓荡凌乱,连背后的纱帐也跟着扭蛇般飘舞起来。
他被风劲顶得微微狭眸,散发飘扬,却任由沁骨的寒意拂掠在身上,习惯了似的仍像平时那样挺着胸膛,昂然伫立。
侧眸瞥过去,左边那扇木牖旁有一道比夜色更深的黑影,半截处却坠着块白玉似的牌子,上面隐隐还有金文篆刻。
裴玄思微撩的唇角向上掠起:“前辈果然是守时守信的人,说来便真的来了,我还道今夜要空等了呢。”
“可裴公子却叫人敲窗敲得心焦,若再多待片刻,老朽便只好自己冒昧进来叨扰了。”窗边的黑影同样“哼”声轻笑。
两人各自打诨似的“交锋”了一阵,算是寒暄过了。
“有伤在身,行动不便,还望前辈海涵。”
裴玄思嘴上致歉,却是一副轻描淡写的口气:“如今这个局面,又是这般天寒地冻的时节,若没有要紧的事,自然也不敢把前辈从热炕头上请到这里来。”
“呵,老朽这十年来辗转各地,餐风露宿,从来就不知道热炕头为何物,哪比得上裴公子香榻软衾,还有绝色美人作伴。”
对方也阴阳怪气的回了一句,跟着便肃声起来:“罢了,有什么事,快说吧。”
这话里讽味十足,裴玄思眼中却丝毫不见冷色,听到“美人作伴”四个字时,脸上反而笑意更浓。
不过,究竟是正话要紧,这时候不再闲扯,当下也正色起来。
“前辈卧薪尝胆,为故太子殿下恪尽臣节,为得匡扶社稷,奉还正朔,我也盼着天日昭彰,讨还血债,眼下时机已成,这盘棋终于到了反击该进招的时候了。”
“哦,你有什么打算?说来听听。”
窗边苍老的语声陡然显出兴致,又带着几分疑惑和戒备。
裴玄思不紧不慢,目光饶有兴味的望着屋后那几株高大的枯树,上面落光了叶子的枝杈越过院墙伸向天空,横在那轮将圆的月上,莫名像把它切割的支离破碎。
“若想奉还正朔,要除去的,一是当今圣上和太子,二就是潞王一脉。如今宫里对潞王府已经起了猜忌,只须再加把火,说不准不必咱们动手,就能将它连根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