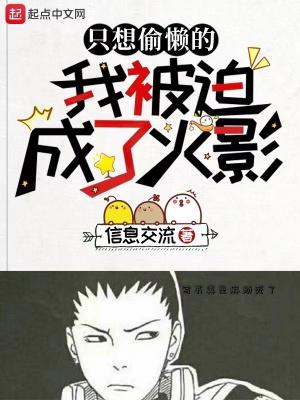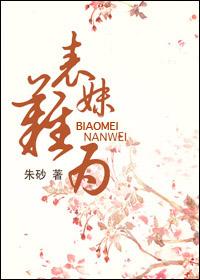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穿成渣男变好的 > 第27章(第1页)
第27章(第1页)
青年看着他,似是想说什么,却终究不发一言,只是张嘴咽下了辛辣的汤汁。一碗汤喝完了,齐元清嘴里尽是汤汁的古怪味道,一杯茶又十分贴心地递了过来,他就着谈锦的手喝完茶,终于将憋在心里的那句问了出来,“为什么?”为什么不生气?为什么会救他?为什么那时明知他要逃还要放他走?为什么突然对他好了起来?太多的为什么,他几乎要以为眼前这个男人是被人下了降头,不然怎么会有如此翻天覆地的改变。
“元清。”那日跳河受了凉,男人的声音也有些哑,“我想待你好。”不谈过去,只谈现在及往后,谈锦是真的想好好待青年。就像他最开始承诺的,帮齐元清赎回母亲遗物,替青年找户好人家,保他下半生安稳无忧,谈锦心里的打算从未变过。即便是舍命救青年后反被他扎了一刀,他依旧是这个想法。那时猛地被扎一刀,说不心寒不生气都是假的,但是下一瞬,那人吓得扔了匕首,抖得像只落水的猫,他便气不起来了。
“你不喜欢我,往后我也少往你面前凑。我已经和黄大夫说好了,等你身体稍好些,就回花溪城住在黄大夫那。要是缺什么少什么就和黄大夫说,不必觉得麻烦他。”谈锦继续道。齐元清那时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显然是不想和他回家。但若住在葭萌城,他实在是鞭长莫及照料不到,这般病弱也不适合再一路奔波回京,回到花溪城住在黄大夫家是最好的去处。
齐元清仔细观察男人的脸色,却没从他脸上瞧出半分情绪,心神恍惚间竟问道:“你生气了?”他也不清楚自己怎么就问出这样一句话,昏头昏脑地。青年有些懊恼地咬着下唇,扯着被子似乎要将脸盖住,但他手上无力,连被子都扯不动。
“我没生气。”只是有一点伤心。但多说无益,况且谈锦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立场去质问或者苛责青年,便没再多话。见齐元清还在扯被子,以为他觉得冷,俯身为他掖好被角,果然摸到被窝里都没什么热度,“冷吗?被子里好像没什么热气。”
青年摇了摇头,几缕乌发垂在脸边,更衬得下巴尖尖,面白如纸。谈锦叹了口气,心知青年心中对自己有成见,定然不会说实话,便推门吩咐安市去找小二放两盆炭火进来。
谈锦自客栈二楼下来,便看见潘南等在下面。
“谈少爷。”潘南将先前谈锦扣在他那的荷包递过去,“愿赌服输。”
“多谢。”谈锦接过荷包,想起那日与潘南举止亲密的步家小少爷,又道:“既然潘相公如此讲信用,我也该厚道些。”他取了一千五百两递给男人,“元清体弱,潘相公近日照料他,定然多有费心。谈氏酒庄是小本生意,手上余钱不多,来日定然重金感谢。”
潘南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不过是顾忌步家打压。但送上门的钱不要白不要,况且他确实在齐元清身上投入良多,便十分坦然地收了银票,转身欲走时,又听谈锦道:“潘相公,请留步。”
……
安市从后厨端了新煎的药,遥遥看见谈锦和小馆里那位长得十分妖艳的男子一道往外边走,心里直犯嘀咕。
他端着药进门,将齐元清扶坐起来,一面喂药一面道:“公子,我觉得谈少爷和从前不大一样了。”
齐元清咳了一声,实在受不了这苦药一勺一勺下咽的滋味,偏头避过伸来的勺子,“为何这么说?”
“公子,难道您看不出来吗?”安市将碗放在一边,公子一向聪慧,怎么如今反倒没他看得透彻,他将谈锦如何与县令巧辩把他救出衙门,谈府中又是安置了多少流民,甚至连谈锦那日自三楼跳窗而下的事都吐了个遍,末了,总结道:“谈少爷如今更有担当也更良善。”他伸手握住青年的手,垂眼替他按|摩指节,似是自语,“如果公子一开始嫁得就是这样的谈少爷,该多好。”
本是轻飘飘的一句话,却沉甸甸地砸进了青年的心里。他想着少年方才的叙述,不像是在谈论他认识的那个谈锦,倒像是在谈论另一个人。可他还未想个明白,便听安市继续道:“不过,虽然谈少爷变好了许多,却也不能算是良配。”
“为何?”齐元清下意识追问道,又在意识到自己问了什么时差点咬了舌头。他这般问,就好像心中已把谈锦看做良配了似的。
“谈少爷实在是太滥情了。”安市摸了摸放在一边的药碗,是正可以大口喝下的温度,便将碗直接递到青年唇边。
苦涩的药汁漫入口中,齐元清听见身边的少年还在絮絮叨叨,“公子,我方才不是说那夜我和谈少爷是坐的画舫来到这葭萌城嘛。”
“嗯。”齐元清接过安市手中的帕子按了按嘴角,秀气的眉毛微微皱着,“他在画舫上与他人欢好了?”
“那倒没有。”少年回忆道:“那画舫上的女子只裹了层薄纱,见了谈少爷便往上蹭,把谈少爷吓得差点落了水。”那时的场景实在好笑,安市当时忍着没敢笑,如今再回忆直接笑出了声。
齐元清见到少年这副模样,眼神暗了暗,却也没说什么,静静听少年继续道:“后来,谈少爷把自己的外袍脱给那女子披上了。或许是碍着我在旁边,一路上竟然十分规矩,坐在蒲团上闭着眼像个出家人似的。”
难怪那时他身上尽是脂粉气。
“他既然如此守规矩,又为何说他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