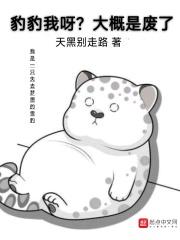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以爱之名电视剧免费观看完整版 > 第8章(第1页)
第8章(第1页)
>
沈阿公和刘建也已来到后院,瞧着这幕两人相视一笑,沈阿公拍拍刘建的背:“谢谢你啊,我这个孙女真心太调皮了。”沈阿婆已经听到自己老伴的话,嗔怪地说:“什么调皮,不过也要谢谢你。”打完招呼各自坐下,沈阿公和刘建在一边品茶,沈阿婆拉着廖文鸾问她过去十年的事。
不过廖文鸾分明是不想讲的,几次用话岔开,既然如此沈阿婆看着坐在一边和沈阿公品茶的刘建,小声问自己外孙女:“你真看上这小子了?囡囡,阿南虽然说做错了些事,可年轻人谁不犯错,你和他又有小竹,囡囡,阿婆年纪大是老古板,觉得还是原配夫妻好。”
廖文鸾伸手抱住阿婆的肩膀摇了摇,就像自己小时候撒娇时候一样:“阿婆才不古板呢,阿婆会上网,有很多网友,还会和阿公一起去旅游,怎么会是老古板呢。”见外孙女答非所问,沈阿婆拍拍她的手:“你啊,尽哄我开心,阿婆说的不是这个。阿南那孩子,我也算看着他从小长大的,有些刚愎自用,但这么些年你走之后他也想到自己的错了,逢年过节也来看我们。”
廖文鸾还是抱着阿婆的肩膀没放开:“阿婆,不是有点刚愎自用,他是非常刚愎自用,而且你真以为我不晓得他做的那些事,这十年他可从来没闲着,真爱一个人,怎么可以去找那么多的情人,别说什么他找的情人都是和我长的有点像,用以排遣寂寞,我不稀罕也不会感动。我的男人,要爱我就要身心都干干净净的,而不是一边叫着爱我另一边去找一些劣质的替代品发泄。”
沈阿婆无奈地张张口:“男人嘛,可我的孙女又怎么能受委屈呢?”廖文鸾笑了:“就知道阿婆对我最好。”沈阿婆抓住她的手:“晓得我对你最好你就忍心一去十年,还让我们打听不到你的消息,要不是这小子经常来陪你阿公下棋,还说辗转知道你的消息,你一切都好。只怕阿婆就熬不到你回来了。”
廖文鸾看着面前的外婆,满头白发像雪一样,是真正的鹤发童颜,又抱住她摇啊摇:“我这不是担心害怕,怕你们骂我,这才躲的远远的。阿婆,你不晓得,这十年我过的其实并不开心。”沈阿婆轻叹一声:“我怎么会不晓得,可你是我们的孙女,怎么会骂你呢,囡囡,到任何时候我都舍不得骂你,我的囡囡是那么乖的囡囡。”
廖文鸾把阿婆抱紧一些,像小时候一样紧紧偎依,阳光透过葡萄架的缝隙洒在她脸上,看着孙女眯紧眼像犯困的猫咪一样,沈阿婆拍拍她的手:“困了就睡会儿,你也别嫌阿婆唠叨,你和阿鸯总是姐妹,有些心结该打开了。说起来,除了能说一句这是时代的错之外,竟然找不到谁错。”
作者有话要说:其实我很讨厌那种寻找替代品表示我很爱你的设定啊。
☆、过往
廖文鸾的眼睁大一些:“阿婆,你在捣糨糊吗?”沈阿婆拍一下外孙女的背轻声叹息,廖文鸾靠在阿婆肩头轻声说:“阿婆,我从来没有心结,是别人有。曾经,我是真的把她当妹妹看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很多时候还不如陌路人,沈阿婆出身大家族,嫁进的也是大家族,八十多年见过听过的这些事情比廖文鸾要多得多,但到此时也只能叹口气,要不是阴差阳错时代变幻,一个乡下穷小子怎么能娶到沈家的小姐?
沈家起于清末,富贵于民国,纵是四九年风云变幻,也依旧屹立不倒,沈阿公的父亲去世于1963年,葬礼无比盛大。可就算如此,有些事也逃不过的。看着孙女闭眼熟睡,沈阿婆把她的手拢一下握在自己手心,八十多年了,时代早就变了,变化的还让人目眩神迷。现在,只要自己儿孙们能平平安安,别的也就不求什么了。富贵荣华,不过是一场泡影,在这座大都市里面来来去去那么多的家族,有富贵过沈家的,大势一变,不也四散开来。就算曾是王侯之尊,享过无边富贵的,今时今日不也落到买不起房子在小屋栖身的地步?
在另一边品茶的沈阿公看向自己老伴这边,瞧着刘建鼻子里哼了一声,刘建感觉说:“老爷子是不是要再下一盘,我可说了,我的棋艺很差很差。”沈阿公鼻子里的气息变重一些:“你这小子,竟然瞒的死死的,这十年连个风都没透,我就不该相信你是君子,要从你这边去查,早就查到我囡囡在哪里了。”
刘建面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惊慌失措:“是,老爷子您说的是,可这不是我的决定,是鸾鸾说的,她说她心乱如麻不想回来见你们,而且您也不知道,刚出去那段时间,鸾鸾连小竹都不想见,每天都沉浸在伤心里面,治病就花了好几年。”沈阿公叹口气:“我晓得,我家囡囡啊,太顺利了,没受过挫折没吃过苦,我本来呢,想着让孩子们摔打摔打也好,怎么也没想到她会做的这么决绝,一去不回。这十年,你不晓得你阿婆抱怨过我多少回,说我心太狠,还说啊,女儿家本来就该娇宠的,当年就对不起阿婉了,现在怎么能对不起囡囡。”
沈阿公背上被人点了一指头,沈阿婆走过来笑着说:“你这老头子,唠唠叨叨个没完没了,我啊,只要孙女回来,还好好的,就什么都不求。”
沈阿公呵呵笑起来,对刘建说:“你瞧瞧,这女人啊宠不得的,到现在我都快九十了,她还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沈阿婆白老头子一眼,这一眼里竟还有几分少女的娇俏:“什么九十,你十二月的生日,到那时候才八十五,别把自己说老了想占我的便宜。”沈阿公哈哈一笑:“瞧瞧,就是这样,我们去下棋吧,臭棋篓子杀起来也有些高兴。”
刘建笑着陪沈阿公去屋里下棋,沈阿婆走到孙女躺着的藤椅边,虽然是睡梦中,廖文鸾的细眉还是微微皱起,好像在克制什么。这十年,外孙女到底发生了什么?
“阿鸾刚出去就被查出有了忧郁症,好在是早期,后来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小牧场住下来,每天都不能离开人,我回国的时候就让女佣和司机二十四小时陪着她。后来因为药物,她又开始发胖,有整整一年时间,所有的镜子都被拆掉。”拆掉镜子,不仅是为了防止发作时候廖文鸾打破镜子用玻璃碎片自杀,更是为了让廖文鸾不要看见镜中的她,从而加重病情。
刘建陷入回忆中,接着就说:“好在阿鸾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那段时间也很快过去了,后来医生又让她到处走走,我们又去了加勒比海,在一个小岛上住了一年,艾瑞克很喜欢那里,后来又去欧洲,不过阿鸾不喜欢欧洲的冬天,这才回到加利福尼亚,一直到现在。”
沈阿婆的手摸上外孙女的脸,触感依旧光滑,可沈阿婆怎么听不出来,刘建那轻描淡写的叙述背后是多么的艰难,自己从小就捧在手心长大的孩子,最困难的时候怎么可以只有一个陌生男人和一个孩子陪在她身边。要知道沈家枝繁叶茂,当初留在这里的只有沈阿公的父亲带了沈阿公这个幼子,沈阿公的长兄,现在沈家家族实际执掌人早在四九年前就带了家人远赴海外。沈家在海外的产业虽不能说遍布各国,也是数大洲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