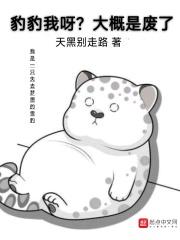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三月里的幸福饼语录 > 第8章(第1页)
第8章(第1页)
>
话,却也显得我们两个都多么在乎。沉默,是最无法掩饰的失落。
车子终于到了学校。
“谢谢你。”我跳下车。
“有一件事,一直想跟你说--”他关掉机车的引擎。
我站在那里,等他开口。
他望着我,欲言又止,终于说:
“对不起,我应该告诉你我有女朋友,我不是故意隐瞒,只是一直不知道怎样说--”
“你不需要告诉我。”我难过地说,“这是你的秘密,况且,我们没发生过什么事--”
我在背包里拿出那个准备送给他的相架来,我一直放在身边。
“在伦敦买的,送给你,祝你永远不要悲伤。”
他接过相架,无奈地望着我。
“这个相架可以放三张照片,将来可以把你、你太太和孩子的照片放上去。”
“谢谢你。”他难过地说。
“不是说过不要悲伤吗?”
他欲语还休。
“不要跟我说再见。”我首先制止他。
他望着我,不知说什么好。
“我要进去了。”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再不进去,我会扑进他怀里,心甘情愿做第三者。
我跑进学校里,不敢再回头看他。
他本来是我的,时光错漏,就流落在另一个女人的生命里,就像家具店里一件给人买下了的家具那样,他
身上已经挂着一个写着‘SOLD’的牌子,有人早一步要了,我来得太迟,即使多么喜欢,也不能把他拿走,
只可以站在那里叹息。
爱,真的是美在无法拥有吗?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方维志,辞去电视台的兼职。
“为什么?”他问我。
“我要准备毕业作品。”我说。
我只是不能再见到文治。
文治也没有找我,也许方维志说得对,负责任的男人是很痛苦的。
良湄在中环一间规模不小的律师楼实习,熊弼留在大学里攻读硕士课程。那天晚上,良湄来我家找我,我
正忙着准备一个星期后举行的毕业生作品比赛。
“你真正就这样放弃?”良湄问我。
“你以为我还可以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