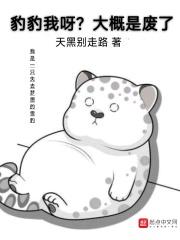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回到唐朝当皇上 > 第19章 意外之喜(第1页)
第19章 意外之喜(第1页)
马上就要入夜了,昏暗的暮色,渐渐降临。小溪场铁做的窝棚下,地炉的火光却依旧炙热,闪动着明亮的光线。明暗交错中,王延兴从军户的帐篷里走了出来,往铁做匠户的茅舍走去。而离此一百多里远的泉郡城内,暮鼓也在阵阵地敲响。马上就要宵禁了,街道上的稀疏的行人开始匆匆地往自家赶。
王审知轻轻地夹了夹马腹,催动马匹小跑起来。才跑了几步,就听到后面有人在唤道:“三郎!请留步!”
王审知回头看去,见是章之源,他勒住马缰,回身拱手道:“原来是章翁!审知有礼了!”
章之源甩开扈从,打马快步赶上,也是拱手:“三郎客气了!”又走了几步,两骑并排,章之源才又小声说道,“那王延兴竟然想去当铁匠,看他日后如何保住这嫡子之位!三郎之助,之源谨记在心,日后,章家定有厚报!”听得出来,言语之中,满是欢喜。
“哼,厚报就免了……”王审知摇了摇头,“某那侄子,似乎有些不同了。现在下定论,为时尚早。”
“哦?三郎是觉得,一个小小铁做,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不成?”
“这倒不是!”王审知继续摇头,他自然是觉得管铁做没有一星半点的前途,才会那般谋划,“只是,总觉得,某那侄子,心中似乎也藏着些什么,某却无法猜透。”
“那要不,乘小溪场荒郊野外之地,派人去……”说着压低了声音,说出几个晦涩不轻的几个字。
“不可!”王审知立即否定道,“章翁可知道,随行护卫的是何人?是邹磐,还领了二十个牙兵。你的人就算得手了,却如何不露马脚?”
“这……”听到邹磐这个名字,章之源就打了退堂鼓。王潮手下有好几员猛将,其中一个满头满脸须发,黑漆漆的大盘子脸的邹磐,更是在泉郡人尽皆知。若是他亲随护卫,那还真没人敢去找麻烦。
王审知点了点头,轻声道:“不要轻举妄动,静观其变!”
听了这话,章之源也只得将心里的想法压住:“全听三郎安排!”
王审知却不再答话,抬头看着天色越发昏暗。不久,暮鼓声毕,泉郡街上,郡兵们开始出动巡逻。再回到小溪场铁做中,同样是昏暗的夜色中,王延兴却正借着火光,刚走到匠户们所住的茅草房旁。
按照后世的标准,匠户应该是这个铁做的核心成员,因为他们掌握着炼铁的技术,是产出效益的人员。然而,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却没有这个意识。谁拳头大,谁发言权就大。就像牙兵欺负军户时的自然而然,在军户面前匠户又成了受欺负的对象。
在牙兵来之前,军户们有土屋住,而匠户们却只能待在土坯茅草房中,便可见一斑。吃食用度,也是比起军户还不如。也就是罗、曾二人没有把事情做绝,私下里卖铁料换来的粮,也分了一点过去。才让他们勉强过活。
无法失去更多时,便对每一点滴的获得都额外感激。当他们得到王延兴分过来的大米后,一个个都是心怀感激。
一锅煮了之后,围在一起吃,有个杂工吃很快,乘别人还没吃完,他就想偷偷地再添一碗,却被罗二一筷子敲在手上,“干活的时候就没见你这么积极!一人只许吃一碗!”
可白花花的大米着实诱惑力不小,那杂工缩了缩挨打的手,求饶道:“大匠!某就添一点点!一点点就好!”
那罗二却是压着嗓子喝道:“不行!某说了吃完这碗,再一起添下一碗!少要聒噪!”
他提起手,还要再打,倒是那章大炉吭声了:“大匠!那衙内就在那边,今日就让他们多吃些许米饭……”或许是听到衙内两个字的原因,那罗二提起的手怏怏地放了下来,章大炉再朝那杂工说道,“黄二!还不谢过大匠赏!”
那杂工连忙低头躬身:“谢大匠赏……谢大匠赏!”说罢,手忙脚乱地从锅里舀了一点米饭,退开一边。
看他碗里确实没有舀太满,罗二才冷哼了一声,对章大炉说:“某说你这个炉头!何苦总是替他们说话?唉!看着他们每日里尽是白烧了炭,又不出铁,某就狠不能将他们饿死几个!”狠厉的目光扫过,一众杂工一个个都把脑袋埋到碗里去了,不敢吱声。
“大匠不必这般忧心,某等又不私藏一两的铁料,确实只炼了这么多铁,某等也是尽力了!”章大炉又劝道。
“某又未尝不知!只是这刺史,先是让人来询问,现在,将衙内都派过来了,让某如何不心焦啊!”罗二说完,又是一阵叹息。
“大匠大可不必心焦!”这却是王延兴接了话,“某来铁做,一不是要问罪,二不是来收铁,而是要与大家一起,将铁做弄得更好!日后,这大米饭呀!不会少了你们的!”
看到王延兴突然出现在一侧,罗二和章大炉连忙起身行礼:“见过衙内!”罗二又道:“奴等心中有愧,恨不能多炼些铁料。只是,这些时日,矿场所处之矿石品质不甚好,出铁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