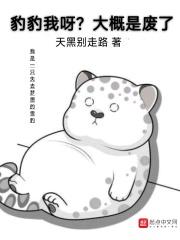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美人瓶的由来 > 第3章(第1页)
第3章(第1页)
>
瓶娘摇摇头。那自称三秀的“小王爷”就一抬手,把头顶的貂皮帽子摘下了。瓶娘还没看清那人的脸,那人就把还带着体温的帽子随手扣在了瓶娘头上。瓶娘乖乖的一动不动。头顶暖洋洋的,瓶娘就笑了。
等瓶娘稍稍把帽子抬起,瞧向那来人的容貌身型,不由得眼睛一亮:
确如其声,那人也是个女子,年纪恰和瓶娘相仿。乌黑的头发梳成扁髻,方才藏在貂皮帽里。再看她身上,将蒙古袍子也解了,现出一身鹅黄衫子杏色裙。本是亮色一抹,灵气却有十二分。
瓶娘脸上还有些羞涩,她却大大方方地立在地上对瓶娘嫣然一笑:
“那貂皮是假的,这身袍子是仿的,白狐裘是班子里的行头,当然也不是真的——我扮相如何?”
说着三秀便眨着眼睛,得意洋洋地看着瓶娘,摆了个身法,作骑马科,十二分英姿飒爽。
瓶娘笑了:“对对,我记得你,上次我在南大门,你就在人群里。”但过了片刻,又是一脸茫然:“什么是扮相?”
“就是扮的小王爷,像不像?”
“瓶娘……不晓得什么是小王爷。到底什么是小王爷?……抵得几个馒头?”
三秀不说话了。她不由得重新打量起眼前这个女孩儿来。一个时辰前,她看见这卖艺女孩儿在十字路口受欺负,就擅自做主赶回戏班子换了一套行头,救了她。可如今又不得不烦恼起这女孩儿的生存去留。不懂什么是扮相也就罢了,在这大都里生活,竟然不知道什么是王爷,实在是令人烦恼。
“三秀?”
瓶娘询问的声音把三秀从思绪里强拽了回来。见瓶娘一脸忧色,三秀释然一笑:“没什么。小王爷不是什么好东西,且不管它。你有落脚的地方么?”
瓶娘脸上现出为难的神色。三秀一见,心中便明白了大半。已经到了这步景况,断然没有再放她回去的道理,最好的主意莫过于……
“师妹!”
三秀正打着主意,忽然听见这声熟悉的呼唤,脸上现出一抹喜色,连忙循声向窄巷口望去。只见马路对面一个脸上还涂满白粉中等身材的男子正一面朝他们挥手,一面躲闪着大路上的车水马龙,往三秀和瓶娘所在的窄巷大步流星走来,不一会儿已经到了二人面前。
还没等来人开口,三秀便抢先道:“大师兄,你怎么来了?今天中午不还要到达鲁花赤老爷的家宴上演戏法么,已经这个时辰,再不去小心迟了。”
“你啊,也就这时候知道关心班里,”被叫做大师兄的把脸立刻把脸拉得老长,“一清早给你派的什么任务?——去西如意村拉行头!你倒好,半路又拐回来,扮了个小王爷出去,什么话也不说。愁杀了咱们班主,让我出来寻你。老实交代,你这回,又惹出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来?”
三秀只是忍着笑一声不响。做出刚才那番行侠仗义的事,她自己心中还得意着,任人怎么说也只是左耳进右耳出,只是低头忍笑,一双大眼睛又不安分地往瓶娘身上瞅着。
瓶娘茫然地站在那儿,全然没注意到三秀的眼色。她只看见眼前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男人,方才还神气活现的三秀转眼乖了下来。瓶娘顿时就没了主意,只能在一旁呆呆地看,又没来由地觉得委屈,眼泪又不争气地打起转儿来。
那三秀的大师兄说了半天,才注意到这里地上还站着一个姑娘,不禁就上下打量了一番:高高的双鬟髻上扣了顶滑稽的貂皮帽,单薄衣裳外头裹着一条狐皮大氅,小身板瑟瑟发抖,更兼以双颊绯红,泫然欲泣的模样,任谁看了都忍不住心声爱怜。那大师兄只道她被人欺负了,顺手就给了低头认罪的师妹一个爆栗:“你这丫头行啊,学小王爷抢女人是不是?”
“哪里的话,我这是‘救风尘’!”三秀猛地抬头,水杏眼瞪成了牛眼。
“‘救风尘’?还‘单刀会’呢!……”那大师兄嘴里念叨着,往地上随意瞟了一眼,恰看见地上搁着的青花瓷瓶,不由得一怔,又抬头看看瓶娘,不禁张大了嘴,半晌没出声。
三秀回头对着依旧一脸茫然的瓶娘眨眨眼,又转过头对大师兄道:“你上次不是说不知道这里有什么机括,想要和她切磋切磋么?喏,我把人给你带来了。”
那大师兄骇然变色,看看眼前的大姑娘,又看看地上的小瓷瓶,一时失语。三秀倒是安之若素:“好啦,知道有这回事就行了。你快去达鲁花赤老爷那儿吧,回来再琢磨。”
大师兄早已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抱起那瓷瓶对着光往里看了又看。倒把瓶娘弄得更加羞涩——好像女孩儿的闺房被外人窥视似的。
“大师兄!”三秀有些不耐烦了。那大师兄才如梦方醒,怀中瓷瓶还不忍释手,道:“这位姑娘……什么时候回去?”
三秀若无其事道:“既然你已经见过了,那当然这就送人回去。”
她这当然是拿大师兄开心的话。可是话音刚落,手就被人拉住了。一转头,三秀看见瓶娘一双眼睛正楚楚可怜地望着自己,手越攥越紧——这小姑娘,认了真了。三秀心想着,忽然有些高兴。
“不行!”大师兄斩钉截铁道,随后又软了下来,“好师妹,你想个办法,留下她罢,起码留她两三天。我也去向班主说情。怎么也得把她的功夫琢磨清楚。”停了一停,又作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这也是待客之礼。你让人家受了惊,怎能不好好安抚她一阵?……只是不知道她那边肯不肯。”
三秀心里知道大师兄已经上了钩,于是就将见瓶娘,救瓶娘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大师兄听说瓶娘素来跟着的中年男人已经弃她独自跑走,这才放了心,道:“既是这样,更加无妨了。依我看,她不如就在咱们介褔班里长住下去算了。师妹,你说呢?”
“我也是这样想的。”三秀说完,转向一边不明就里的女孩儿,灿然一笑,“瓶娘,你可愿意到我们介褔班来?也就是添双筷子。”
大师兄也在一旁帮腔:“师妹她一个人一间屋,我们正嫌她占地太大呢。你来了,正好和她一起住。”
瓶娘虽然还是懵懵懂懂的,但听见“一起住”三字,便知道自己有了着落,竟然双膝一软,就要跪下。好在三秀眼疾手快,抱住了她的腰:“好端端的跪甚么,往后就是姐妹了。一起走罢。”瓶娘羞涩地歪在她肩头,允了下来。
大师兄正喜不自胜,忽地想起什么,回头看看日影,道:“不早了,我真得走了。对了师妹,班主交待,若遇见你,叫你赶紧回去看新曲儿。程笑卿新写了几支曲儿,现在人应该还没走。”
三秀点头,怀里还倚着瓶娘:“我也正准备让他给瓶娘看看伤。那贼老奴!竟用石头打小姑娘的头。”说着,手就轻轻覆在了瓶娘的伤处。
瓶娘这些年来第一次在大街上行走,两眼里都是惊喜与好奇。揭开馄饨锅盖冒出的腾腾白气,等着打羊羔酒的人们排起的长龙,蒙古女人头顶高高的姑姑帽(注1),铁匠铺里正淬火的通红马掌。她从来没见过这些。先前那男人无论带她到什么地方,都是用布袋蒙住她,到了目的地才放她出来。她只能在黑暗里听见馄饨摊的喧闹,铁锤的铿锵,女人嘴里叽里咕噜的蒙语和醉汉颠倒糊涂的骂街。瓶娘不知不觉就慢了脚步,又不知不觉就停了下来。三秀几次拖了她的衣袖,提醒她快走。后来索性就扶她上马,任着瓶娘一路指点着两边的情景问这问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