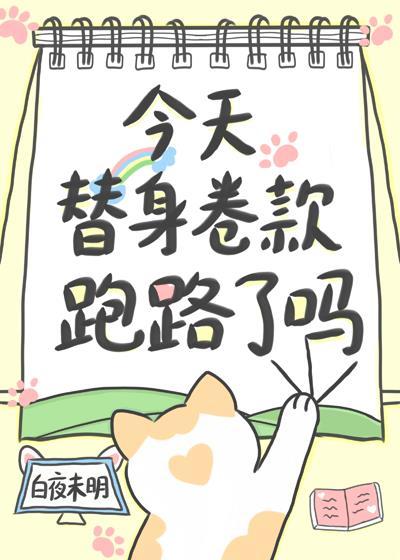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锦食记宅包讲啥 > 第50章(第1页)
第50章(第1页)
>
虽然不清楚他的酒量如何,但她看得出他的精神是不太好的,在饮完一瓶的烈酒后走路竟然有些摇晃的样子。她发誓在他拖着步伐走进卧室时差一点撞了上门框,她是咬着舌头才忍住没叫出声来。他扶着门框稳了稳,背部隐约看得出紧张的肌肉轮廓,如同他今天的情绪,压抑阴郁,躁动不安。
她终是没忍住,开口问道,“你还好吧。”
“你紧张我吗?”他转过身来一字一顿地问道。
她一时语塞,知道有些人喝醉了酒并不是胡言乱语而是口齿清晰地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虽然条理分明,但依然是醉话——就像眼前的单衍修,现在就睁着眼睛说醉话。
“你喝醉了。”看着他泛红的脸颊,她总结道。
同样的,被认定醉酒的男人很干脆地给出千篇一律的反驳,“我没醉。”
“通常人说我没醉的时候就是醉了。”
他顿了顿,湿润的眼睛慢慢地眯了起来,“那我醉了。”
“你的确醉了。”她点头。
他拧起眉毛,弓起手指敲着门框咚咚响,“胡说八道。”说没醉是醉了,说醉了也是醉了,什么鬼逻辑。
和醉了酒的人争执其实是件蠢事,她很快便妥协了,“好吧,你没醉,赶紧去休息吧。”
“我没醉为什么要去休息?”
她噎了噎,险些没吐血,“好好,那不休息,你就站着好了。”转身去收拾酒瓶和酒杯,收拾完后又将窗帘和落地窗拉开透气。外面此时已经是阳光灿烂,她往下看了看,肌肉男和井言已经不在了,楼下一片寂静。
于是,肌肉男还活着吗?
她的八卦之火尚未熄灭,RP是轰轰地往外冒。正打算偷溜下楼去探个究竟,未料扭头却看见单衍修竟然还半闭着眼倚在卧室的门边,身体依然是摇摇晃晃的。
“你干嘛不进卧室啊?”
“你不是让我站着吗?”
完蛋了,这不止是醉到脑袋不清醒,连人格都醉得分裂了。雅晓大着胆子上前戳戳他的肩膀,“嗳,那现在我让你你进去睡觉好不好?到床上去睡。”
“好。”
见他乖乖转身进去了躺下了,她才过去替他盖好毯子退了出来。想想有些不放心,又进去把床头灯拧亮。他想来是醉得厉害了,手抬起半遮着眼很是疲累的样子。就着灯光她这才看见他的手心里有一道半长不短的血痕,像是利刃划出来的,伤口并不深,血液也已经凝固了。她没有考虑太久,转到储物间拿了小药箱出来,药箱里放的多是口服类药物,她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小包棉签与半瓶药用酒精。简单的清洗消毒了伤口,没有外敷用的药粉药膏也没有见惯的邦迪。只好将止痛片磨碎了敷在上面,管它有没有用。
在这过程中他依然是沉沉地睡着,呼吸细密而均匀。这个男人即使是在睡觉的时候也不会放松,眉峰习惯性地拢聚起来,仿佛睡眠也是件不太痛快的事。她不自觉地抬手虚敷在他眼上,掌心正对着他的眉心,慢慢地贴合上。
她不喜欢他的眼睛,太犀利尖锐,这让她从来没有办法在他面前掩饰些什么。在某些时候他从不掩饰锋芒,他看透世故却不圆滑,行事从容却总是带着刚硬和强势,她觉得他几乎就是个从不懂得退让的人。这样的人就像是一块切割方正的石头,有着绝不妥协的棱角。
她觉得自己最近的心思有些乱,像是一团没有头绪的毛线球似地满地打滚绕圈。有时会觉得很烦燥,如同上学的时候某天睡到半夜突然醒来想起一道很难的数学题目,便这么一直思考着直到天亮。她隐约感到这不是一个好的兆头,有种未知的东西正缓慢而坚定地侵袭着她的理智,时不时搅乱她的思绪,甚至会影响她的判断,让她做出一些莫名奇妙的举动来。就好似刚才问他要不要吃煎蛋,没事找事地替他上药。其实这些她可以不必去做,他也从没要求她做过,显然是她鸡婆了。莫非真是因为长期被他压迫,就这么被驯养习惯了自发自觉地当M吗?
不,应该不是。
正当她心潮翻搅之际,熟睡中的男人突然翻了个身,手臂自然地扬起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弧线——
“啪!”
平白挨了一个不轻不重的耳光让她当场呆愣了几秒,旋即腾一下站了起来。如果单衍修是爬行动物类,那他现在会是只刺猬。如果他是鱼类,那现在便会是条胀气的河豚。但,或许茹素的妖孽会更喜欢板栗或是红毛丹这样的形容吧。总之熟睡中的单衍修是被雅晓的目光给扎得一身是洞,她气得发抖可又无处纾解,四下张望了一下,伸手捞过一颗大枕头砸在他脸上,
“王八蛋!”
刚才就不该给他上药,让他就这么破伤风死了算了!
一盒黄瓜
把土豆削干净切成小块煮熟后捞起晾凉,用勺子压成泥后分成两份;一份用滤勺滤出,准备做冷汤。冷汤原来是要放牛奶的,她改了方子加入蕃茄炖汁慢慢地搅开来。味道闻起来还可以,她舔了舔调味勺子,唔,好像酸了一点,凑和凑和啦。另一份的土豆泥是加入面粉、红萝卜丝和洋葱末做成饼下锅煎,煎之前她还撒了把蒜末进去爆香。
“今天就是这些了,”她主食和汤分好小份各自摆好,“送货公司的打电话来说送货员半路上出事骨折了,人安排不过来。冰箱里就剩土豆和一点零碎了,将就一下吧。”
“你脸怎么了?”他看着她,“被烫了?”
她抬起眼皮甩给他一个白眼,“你打的,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