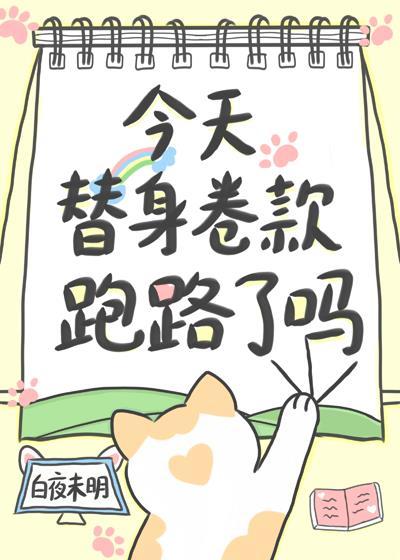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禽兽不如打一生肖 > 第79章(第1页)
第79章(第1页)
>
下午的时光是最美好的,他会让她把脑袋枕在自己膝上,用手指梳理她略长长的头发,偶尔也会亲昵地捻揉她小小的耳珠。她半闭着眼睛享受着这难得的待遇,听他和自己说话。聊天聊地聊八卦闲事,有时也会掂本书念给她听。他的声音低沉,读到深沉处几乎变得暗哑,像没入沙子的水珠般消匿无声。
“……我问她,怎样才算是长久?她说,如果真是他,一霎便是长久。”
这本被她从沙发边缝翻出来的书早已没了封面与扉页,连书页都萎黄残破。在他印象里她并不是个言情浪漫的姑娘,可是那天却缠着他,让他读给她听。
“……那些岁月已经离得很远了,危险恐怖又血腥满途。可奇怪的是她从来没做过恶梦,一闭眼便只有黑暗。她习惯在黑暗中生活,那是最令她安定的颜色。……终究到了离别的时候,可是任由她怎么想,也绝没料到是会以这样的方式。叛痛的伤痕掩在模糊的血肉之下,最后被烧化成了灰……可她还能闭上眼睛后再睁开,于是便继续活下去。何况,她还懂得如何欢笑与快乐……”
他虽然是个感性的男人,却并不喜欢这样的书。华丽的词汇以一种令常人不便阅读的生涩排列方法组合在一起,拗口而晦涩。似乎作者总是喜欢将自己的小心思藏在只言片语中,让读者捉迷藏似地去捉摸揣测,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游戏。
读完第三遍,她已经熟睡。这些日子好汤好水养着,高床软榻人肉抱枕伺候着,她连脸都圆了一圈,看着竟然有些珠圆玉润的感觉。他小心地将她的脑袋托起挪到毯子上,又给披了层毛巾被。刚站起来欲走,裤角又被她拖住。他目光往下,她圆滚滚的眼睛像两枚玻璃弹珠,隐约有水波的纹路在里面荡漾。
“你怎么什么都不问?”她说。
他的唇动了动,最后紧紧地抿起。老爷子寿宴那天,宁珅与她的熟络看在许多人的眼里。当晚陆云德便找他谈话,各种消息纷至沓搅在一起,分不清真假。陆云德早年曾供职于某机密部门,总是有些特殊的渠道。可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将她的底细打听得真切,这怎么能让人放心。
“这姑娘不简单。”陆云德这么说道,“你要谨慎。”
可要怎么谨慎呢?任凭他再怎么谨慎想不到,在谈完话后不到三小时,她便突破了大院外的重围,势如破竹地袭进他的房间。
有她在的地方,谨慎总会变成个笑话。
“我以为你至少会问,我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她说,“原本一直怕,可是现在,却又怕你不问了。”
他眼睫低垂,目光微黯。他们的身体已经有了最亲密的接触,但不代表着可以肆意探挖彼此的心灵。实质与精神可以融合也必然有隔阂,每个人都有一生都不愿示人的秘密。她只待他问而不主动提,这样的坦白总像是带着强迫,所以他宁愿沉默。
可是她不说,不代表着他一无所知。事实上大前天康路路才组了场鸿门宴款待他,他踌躇再三还是瞒着她去了。加上他,十五人的圆桌座无虚席。席间面孔或熟悉或陌生。扪心而说,无一不出众优秀。众人表情各异,神色不一。
入席后竟然沉默了有近一刻钟那么久,恐怕他这一生都难以忘记被一众人列席围观的场景。他竟然没有当场暴走或是落荒而逃,实属勇气可嘉。
康路路说既然她选择了你,那么我们这些前辈有必要给你一些参考意见。你看某某和某某,都是千里迢迢风尘仆仆赶回来的。大家时间宝贵,凑齐不容易,只为让你更充分地认识到你要面对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男人们有的话多,有的话少,情绪都还算平和。她的过去背景也一点一点地剥了开来,完整地铺陈在他眼前。
纵横联盟最危险部门的核心成员,最优秀的‘行刑者’。
他倒是有听说过纵横联盟,数十年前发迹于国外的华人组织,架构庞大且神秘。难怪她会有那样的身手,那样的果断狠辣,又有那样的累累伤痕。
“她倒不是个花心的人。”突然有男人替她说话,“不过喜新厌旧的速度快了些。”
“不,”又有男人反驳,“她这种行为就是狗熊掰棒子,一路掰一路丢,最后攥在手里的只能是瘦蔫货。”
“总之风格就是短稳快,”还有人补充,“时间短过程稳处理快。”
讨论是需要氛围的,当大家讨伐的对象相同时,很容易产生同仇敌忾的心理。一时间桌上嗡嗡声一片,热闹又不失优雅。
恐怕他再活个百十来年也碰不到这种场面——还是自己当主角的。
末了由康路路作总结,“不论从哪方面说,在座的没一个比你差。可‘我们是谁’对她来说并不重要。”他略一停顿,“这里的每一个都合适她,可是全没赶在最好的时候。”
“你很幸运。”
在她对爱情的认知最成熟的时候,却是遇见了你。
这便是你的运气。
现在他的运气正匍甸于他脚边,眼睛圆溜溜地瞪视着他。在那一刻他突然思维跳跃地想到,倘若运气想要溜走,他该怎么办?不过一瞬间的心神恍惚,下面的人便叫嚷起来,“不问就算了,干嘛踩我?”
当然要踩住了,他想,踩紧点就溜不走了。
静夜原本是想趁自己大病初愈的时候和他坦陈一些事,她知道他是个感性的男人,所以心很软。在这个时候把自己那不太光彩的过去全抖落干净了,接受度较高。可她没料到的是自己早被人揭了老底,还附赠了一堆闲言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