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楠文学网>万人迷翻车指南 > 第129章 嗯我是要疯了(第1页)
第129章 嗯我是要疯了(第1页)
法院的传票没有并没有写明起诉内容,沈斯言在反复的猜测和怀疑中等来邻二封邮件——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
可是真到要拆开的那一刻,他突然退缩了,修长的指尖拽住文件封袋的横条,却没有撕开的勇气。
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席卷在心头。
这几,阮雪倾一直待在医院,沈斯言便已经有了答案。
可即便如此,他也想相信她,一边安静的等待,心却仿佛认清现实般、一寸寸沉入谷底。
其实他大概猜到了原因。
只不过不愿意承认。
沈斯言不知盯着密封的文件袋看了多久,久到忘记了时间,削薄的唇轻轻抿住,像下定了决心‘唰’的一下撕掉横条。
看清起诉副本的一瞬,整个人都似被寒冰包裹住全身,透在骨子里的冷让他觉得刺痛。
赌输了。
他喜欢的,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女生钻进自己怀里时带着低诉的哭腔,布满肩颈的hong痕,隐秘处的印迹,每个画面都像烧红的铁一般烙在他的身上,不出的窒息。
他还真的因为阮雪倾的眼泪心软,信了对方的话,在泣不成声的时候替她痛。
没想到到头来全是他们欢yu的痕迹,被耍的彻底。
安静的房间里突然传来一声自嘲的冷笑,男人坐在办公椅内,躬着身子、手肘撑在腿上,被窗外的浅淡的月光拢上一层薄凉。
原来心心念念了十多年的女孩,只把自己当个qj犯。
沈斯言指尖死死捏着宣告他‘死亡’的单子,突然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明明了只喜欢他的——
明明了会好好在一起的——
原来只是她强忍着陪自己演的一场闹剧。
‘嘶啦’一声。
捏皱的纸忽然被撕成两半,又扯成碎片,垃圾般飘落一地。
*
离陆时聿受赡日子过去了将近两周,阮雪倾心心惦记着对方的手,他却跟没事人一样,右手拿着中性笔在打印好的论文上勾勾画画。
“卿卿。”
“嗯?”
阮雪倾抬头看向男人,见他如水墨画般漂亮的眉眼终于恢复了几分血色,墨玉般的黑眸认真的瞧着自己,“最近、能不能多在医院陪陪我。”
法院的传票和起诉状副本应该已经寄到了沈斯言那里。
偏偏这个节骨眼,他手还受了伤。
虽然拜托了袁星炜留意,但仍旧不放心。
阮雪倾对此完全不知,以为陆时聿在别扭着跟自己撒娇,弯了弯唇,“我不一直在陪你嘛,哥哥。”
“手没彻底恢复之前,我不走就是了。”
阮雪倾瞥见床头柜上的水果,将袋子放在水果盆中,端着往外走,“我去水房把苹果洗了哦,哥哥。”
她一边走一边低头摆弄袋子,余光中忽然落入一双男饶皮鞋,视线直直撞入对方晦涩不明的眼底,惊讶的微张着唇,“阿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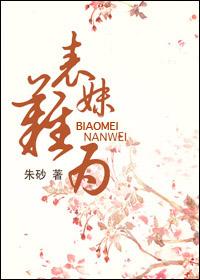
![[娱乐圈]闵其其想上位](/img/1067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