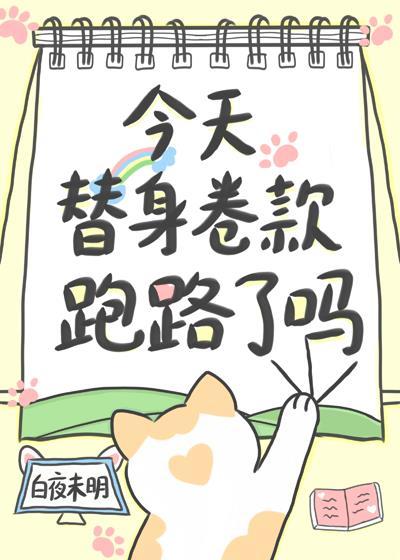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恩客 半缘修道讲的什么 > 第55章(第1页)
第55章(第1页)
>
卞晨还想再说些什么,但是被陈岁云打断了,“你怎么会认得韩龄春?”
卞晨就道:“他来我们学校上台发言过,是我们学校的股东之一。”
陈岁云又问:“还有别人知道韩龄春的身份么。”
卞晨摇摇头,“除了我,应该都不知道罢,裁缝家的记者都说不清他的来历。”
陈岁云点点头,他在人际场混迹多年,三两句话便打发走了卞晨。
陈岁云回到楼上,韩龄春正在八角亭安置他那两盆花,衣袖卷着,露出线条流畅的小臂。
他把卞晨如何认出韩龄春的事情说了,又道:“不过他答应我不对外人说。”
韩龄春手上沾着土,回身看了陈岁云一眼,“卞晨是不是喜欢你。”
陈岁云一愣,脸上浮现些恼怒之色,“你在想什么!”
韩龄春道:“合理推测。”
陈岁云嗤笑一声,“卞晨有点叛逆,弄堂里的人连他爸妈都不理解他。我虽然也不理解,但到底没有嘲笑过他,就这样攒下来的交情。”
韩龄春也不知道信没信,仍在摆弄着花草。陈岁云一见了他这样子就烦,推他下楼,“甩脸色给谁看呢!”
陈岁云态度真差,韩龄春被推出来,心道,这才是他的真面目,不精致,不善解人意,最嫌弃人矫情,倔起来能折腾死人的臭脾气。
韩龄春觉得这样的陈岁云有了些年轻时候的鲜活。
外面又下雨了,他搬了把椅子坐在客堂,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听雨。希望今天晚上能凉快一些,这样他才得上陈岁云的床。
一连下了几天雨,总算等到了放晴,家家户户都把潮湿的衣裳被褥拿出来晾晒。晒台上,韩龄春架好竹竿,把衣裳薄毯抖落开,晾在竹竿上。
不止陈岁云一家,站在晒台上往四周望,每家的晒台上都挂满了衣服。夏天的衣服都很轻薄,颜色也鲜亮一些,灿烂的阳光下布料迎风招展,别提多漂亮了。
陈岁云不在家,他出门溜达去了。这会儿是清晨,还不算太热,裁缝门口的麻将桌上已经坐上了人。
陈岁云穿着一身烟灰色真丝长衫,一只手抓麻将牌,一只手摇着折扇,翘着腿,玩着牌,不亦乐乎。
孙太太送走小女儿上学,这会儿也摇着小扇子挪过来,她穿着一件无袖的花旗袍,露出雪白丰腴的两个臂膀,额头都是汗,止也止不住。
“哎呦,这天气可真热。”孙太太畏热,站在裁缝铺子里头,太阳晒不到的地方。
“谁说不是?夏天真难熬。”陈岁云打出一张牌。
孙太太摇着扇子,“怎么就你,韩先生不出来走走?老是下雨,人都闷得发霉了。”
“他在晾衣服,马上就下来。”
有卖荷包的小姑娘过来,凑在人群里,怯生生问道,“要不要荷包?”
孙太太拿来一个瞧,荷包花纹不甚新奇,但是做工还算精细。荷包里装着花,放在衣柜里熏衣服,去霉味。有丁香花,栀子花,茉莉花的,香味儿很雅致。
陈岁云拿起一个丁香花的闻了闻,他记得韩公馆用作熏衣服的香料就是丁香花,一进衣帽间,丁香花的味道丝丝缕缕。
“给我来几个。”陈岁云挑拣了三四个。
孙太太道:“倒不必买她的,拿些零碎布头自己缝一缝也没差。”
陈岁云笑道:“你看我可是会做针线的人啊。”
孙太太明白过来,笑道:“那你挑罢,可不要忘了给韩先生也带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