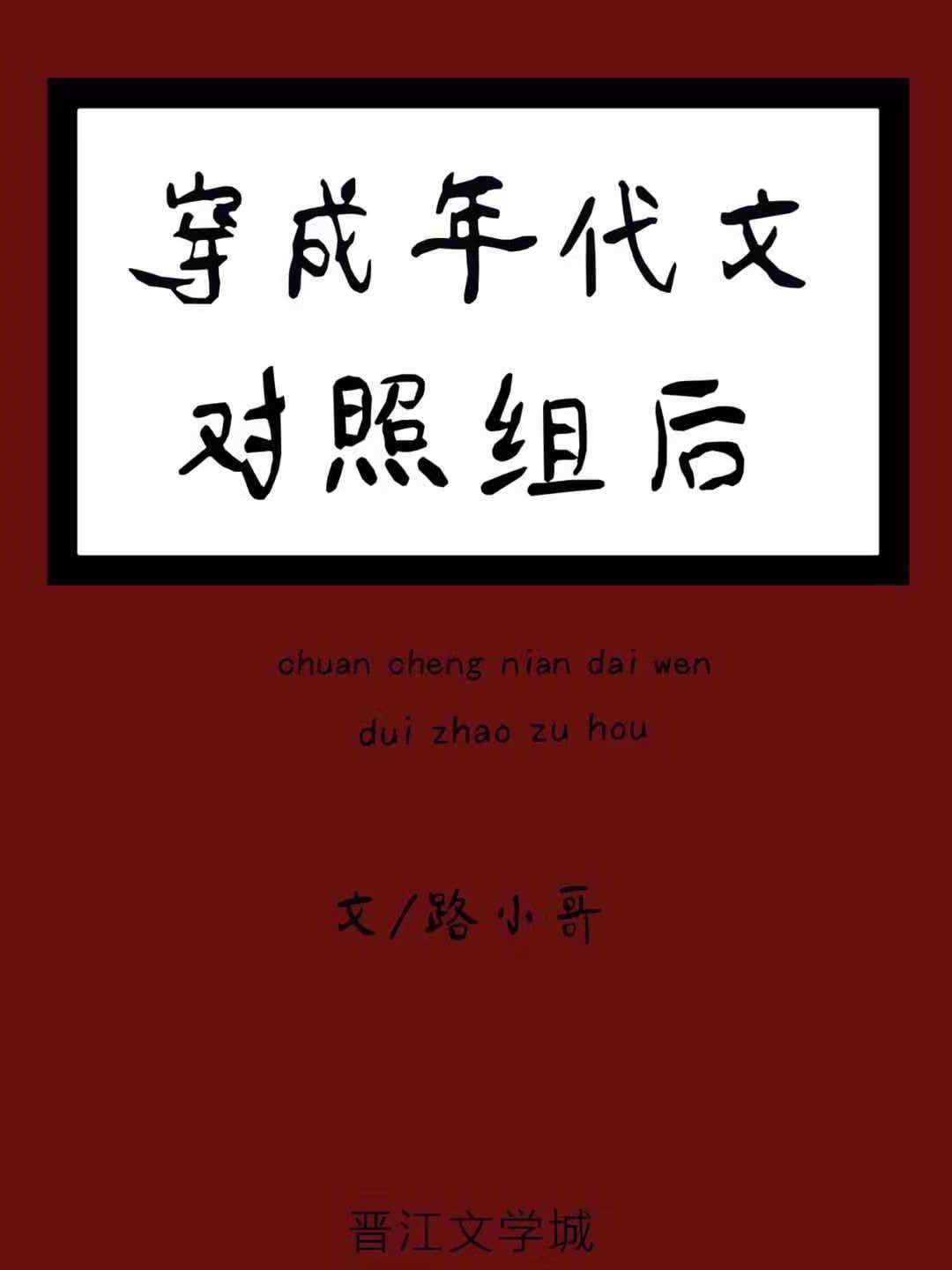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上仙有劫谢佛池梦到苏时镜吃醋 > 第54章 臭棋篓子(第1页)
第54章 臭棋篓子(第1页)
次日一早,泊在岸边的船照常出。昱州一行也只是个小小的插曲,唯有小皇帝垂钓时问了一个城民那知州的名字,而后写在了一张纸上放入了袖子里。
晏画好奇,他仰脸一笑,“等朕回去给你报仇呀。”
晏画噗嗤笑了,“你回去都不一定记得这些事。”
小皇帝挠挠头,“是吗?”顿了下,“没关系,朕会努力记住的。”
说完又拿起那张纸,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几遍。晏画口中含着蜜饯,吃吃笑着他是个傻木头人。
船又开始破浪而行了,只是不知为何,每过一个关隘,都要被仔细盘查,路上又耽搁了许多天。
妖仆们这次学乖了,买上许许多多的食材在船上,只可惜妖怪的口味和仙人的不大一样,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奇奇怪怪的味道。
晏画仙子为此没少同闻昼妖君吵架,不过谢拂池是一句多的也不能从晏画口中撬出来。此去淮都,路上的时间也不短,谢拂池没有八卦可听,闲得无聊,将白诃又一顿收拾。
“你那天是不是感知到了栖弋,才死活不肯下船?”
白诃表情委屈,“他们那天钓到的鱼里有魔气,吾不知道是谁,但吾不想让人看到吾如今的处境。”
谢拂池觉他确实没说谎,遂指了指自己终于开始变浅的咬痕,“这是什么?”
白诃认真端详,“不是吾咬的。”
“……我真的会弄死你。”
白诃这才老实回答,“可能是她分身里藏的魔毒。”
谢拂池一愣,“我没感觉到中毒了。”
“当然。因为这个毒会侵入心府,像你这种仙心都碎了的人,要好久好久以后才会作,不过也不一定有毒,那只是个分身。”
谢拂池心情复杂。她完全没想到自己竟还有这种误打误撞的好运。
白诃以为她难过,宽慰道:“不过你别太担心,化身里藏的毒不会太多,顶多法力尽失,变成废人。”
“我觉自己对魔界一直有着误解。”
“嗯?”魔君天真且懵懂地抬头。
谢拂池慈爱地撸了他一把,“你能活这么大且能坐上魔君,足以说明魔界如今的堕落。”
白诃急忙将爪子搭在她手臂上,阻止她的动作,反驳道:“吾之一族的力量皆系于魔尊,若非尊上失踪已久,时嬴又岂是吾的对手?”
这种话谢拂池已经快听腻了,不过白诃于她还有用处,遂只好面无表情地又听他描述了一遍魔尊当年的辉煌战功,那是如何的英姿勃,气宇轩昂,卓尔不凡……
谢拂池觉着迟早要把他涮了,否则自己一定会被念叨死。
一路或听着白诃碎碎念,或听着晏画与闻昼斗嘴打架,及将至淮都时,已是五月末。
船头一声“噗通”,显然是有人落水。
晏画尖叫一声,“闻昼,这已经是你第十三次将他踢下去了!”
谢拂池被吵的脑壳痛,揉了揉额头,又懒洋洋地伏在桌上落下个子,目光却落在桌子上一串青葡萄上。
这个季节的葡萄还有些酸涩,但晶莹剔透,用来装点门面却是不错。
“今日先下到这。”
对面的人忽而开口,谢拂池从善如流地放下棋子,一脸无辜地将白衣神君望着,好像要来与他下棋的不是自己,“怎么?你嫌我棋艺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