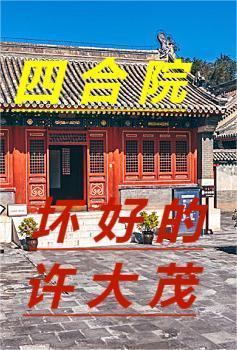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原神钟离x魈cp > 第138章(第2页)
第138章(第2页)
“你在生气。”
“不敢。”
钟离不作声,长睫低垂,眸光轻落在你脖颈上,过来拉你的手。
看到他这副模样,你就算有天大的火气,也平复下来。
你注意到身后躲闪的几双眼睛,深吸一口气,反握住他的手腕。
“我们到里面再谈。”
与吾妻书
……
白衣苍狗,日月如梭,政务厅也再不似从前简朴,几经扩建,庭院大了不少,大概是因为钟离忙于政务,久居于此,厅后还建了间供他休憩的的小院。
院落中栽着两株却砂树,亭亭如盖,浓荫遮去大半庭院,朝西的支摘窗下霓裳丛生,挺拔的竹节拱卫在花团两侧,几经春洗,枝叶如碧。
你迈进正堂,目光落在书案后几排高大的书架上。
钟离正同千岩军交代些什么,背对着你,肩背挺拔,墨玉似的长发梳成一束,扣以金玉,垂在身后,发尾耀眼的金色直叫天光逼退。
你看了他一会儿,收回视线,走到靠墙的书架前,略过层层书卷,目光落在犄角旮旯处的抽屉上。
抽屉上挂着一把青铜小锁。
你盯了它一会儿,抬手摸了摸锁梁,一道金色岩印浮现,又很快隐没,一声清脆的弹响后,锁开了。
它这样盛情邀请,你也只得却之不恭。
你撩起眼皮,偷偷看一眼钟离,背过身,抽出抽屉,目光倏然凝住。
这其中既不是寻常的经史子集,策论文章,也不是什么名儒大作,奇珍异宝,而是一叠叠色彩纷呈的笺纸。
杏红,明黄,浅青,残云……色泽或浓郁饱满,或清朗淡然,印着形态各异的拱花,镂刻着花鸟、山水,十分精致,规规整整的叠在一起,许多已不是如今时兴的模样,像是把笺纸的变迁史都收纳——最靠里的几沓边角微卷,俨然算是老物件了。
但总有一样是不变的。
你指尖微颤,极轻地抚上顶端的信笺,墨痕明亮,落笔之人十分慎重,字迹端正,铁画银钩,并无分毫余墨氤出。
你嘴唇蠕动,无声地念起封上字迹。
与吾妻书——二十二年写于归离集。
与吾妻书——三十七年写于玉京台。
与吾妻书——三十九年写于珉林……
你只觉得浑身都在颤,掀开最顶端的信笺,并未打开,只执拗地向下翻过去。
与吾妻书,与吾妻书……
一遍,两遍……
一千七百年的时光静静地藏在这方寸之间,于一个寻常初夏,尘埃沾染金霞,为你所惊扰,随着信笺一封封翻过去,时光也就倒流回从前。
它已沉寂一千七百年。
于是思念如潮,顷刻将你淹没。
春意阑珊,信笺便取浅红,落着杏花微雨的纹路。冬雪连绵,信笺便似残云,镂着霜雪万点。
东海扬尘,陵谷沧桑。
抽屉恐施了仙术,远比看上去深,待你翻开最后一纸信笺,墨迹已自鲜亮趋于青黄——战时的璃月笔墨匮乏,歌尘自归离集带回的这方松烟墨,已是难得清亮,只可惜终究被岁月篡去色泽。
它已深藏此处一千七百余年。
你忍下眼眶泛起的热意,将信笺依次排好,随后直起身子,推回抽屉,于是几千几万封书信重归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