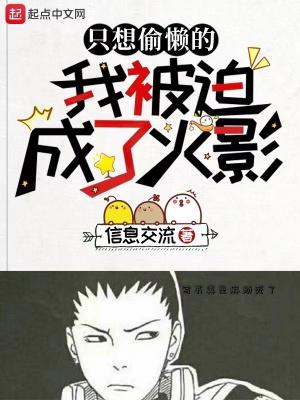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中国第一通缉犯名字 > 47 第 47 章(第2页)
47 第 47 章(第2页)
他问:“你们在干什么?”
安娜探出头,看见并排站着的丁棋和陈小花。
丁棋手里拿着一杯水,回答:“给你接水,不过看样子你也不需要躺在床上,等人把水端过去。”
金小竺把自己的耳朵拯救出来,气道:“谁要你端水了,不是,我刚刚……看见你们两个……”
“我们?”丁棋走上前,把水杯递给金小竺:“我和陈医生吗?我们怎么了?”
金小竺没接那杯水,被安娜一把塞进怀里。
他急忙捧起水杯,免得打湿衣服。
听见丁棋说:“安娜,我们先回去休息吧,你一晚上没睡。”
金小竺一看,急了:“你别拉安娜的手,你刚刚还拉陈医生手呢?”
丁棋诧异地抬眸。
陈小花同样满脸问号,问道:“你烧糊涂了?说什么胡话?我都不认识别人,我拉什么手?”
“可是刚刚……”
“金小竺,够了。”安娜冷下脸,余光都不再看向他,面无表情道,“你好好养病,我们先走了。”
……
安静的华丽的房间内。
微弱的皮肉被剌开的声音响起。
随即,一道呼吸变得急促。
尼兹灌下一杯酒,红色的酒液顺着嘴角淌下,滴入已被鲜血染红的被单上。
他贪婪地嗅着血腥气味,一双眼睛似乎黏在了被重新切开的伤疤上。
越人践被剧烈的痛感折磨醒来。
一双眼睛沉重地睁不开,痛感越清晰,大脑越是混沌。
仿佛溺水的人,又仿佛陷入泥沼的人。
沉重地往下坠落,窒息,冰冷,无力挣扎,只能清楚地感知到,死亡的气息与潮湿恶臭一起,从皮肉侵入灵魂。
“醒了?”尼兹惊讶道。
他饶有兴趣地望着越人践费力掀起的眼皮,表情说不清是失望还是兴奋。
“天……亮了。”越人践沙哑的艰难地吐出几个字。
尼兹朝窗口瞥了一眼,肯定道:“是啊,天都亮了。”
“我本来是打算昨晚就把你放进玻璃罐的,可惜……哼。”
他哼笑一声,摇晃酒杯:“昨晚派出去的人又被抓了,一群废物!”
“我一不高兴,酒喝多了,就把事儿耽搁到了现在。”
尼兹转过脸,目光定在越人践被割开的伤疤上,逐渐浮现出痴迷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