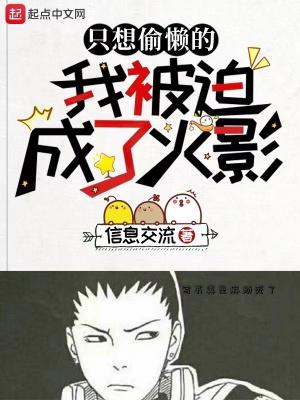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排球少年 乙女向 > 昼神幸郎星星落下的那天六(第3页)
昼神幸郎星星落下的那天六(第3页)
放弃奢望神降的凡人。
真实地面对这个世界,好难的课题。我无法当自己的神明。不可冒犯,不可诱惑,不可动摇……我做不到。我没找到让我变成这样的东西。我只能做到去找寻更适合我的东西,而这东西不是我的喜爱之物。
昼神幸郎不也是吗。嘴上说着喜欢,难道他真的很喜欢送走动物的生命的感觉吗。难道他真的热爱兽医学吗。这个国家的哪个人是为了救治生命而学医的?难道没人和他说过“你脑袋聪明,适合去学医”吗。难道没人劝他“正好,你有养宠物狗的经历,可以去当宠物医生吗”。
我不信。
没有热爱,真的能做自己吗?
不。
正因为没有热爱,才能全心全意爱自己吗。
热爱之物与己身是分离的吗?
为什么「星海光来」能做到一致?
“凡人……”昼神幸郎想起了我讨厌的同类的全称,补上了,“信徒。”
“没错。”
我才不愿意去同情昼神幸郎。一如我不愿意同情自己,所以才会自我折磨,比任何人都要不尊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或许因是别人种下的,但果只有我自己才能承担。如果连我自己都可怜自己了,那我该怎么说服自己活下去呢?——浅薄的想法,分量轻到一只海鸥飞过带来的气流就能掀翻。
我已经开始相信,我可以学习海鸥飞行的轨迹,在地面上行进。即是说,我承认,我的不在意与「星海光来」的不在意是两种东西,我的那份是一种缺失,而非强大。我开始可怜我自己了,并且,希望通过爱护自己,建立尊严感,学习感到被冒犯、学习发怒、学习大叫着拒绝他人对我说出“真可怜”。这一切不仅是因为「星海光来」没有对我说出“真可怜”,还因为,昼神幸郎对我说出了“真可怜”。
这句“真可怜”是昼神幸郎被我说“讨厌”的契机,曾经他在被无视和被讨厌之间选择了被讨厌,而我怀疑他早就发现讨厌的含量不纯了,因为他说:“我不当信徒了。”
“你就没当过吧。”向来和星海光来勾肩搭背的、吵吵嚷嚷的。
“不是说光来君的,我是在说神同学你。”
我就知道,我们对“神”的认识出现了点偏差。我无法从镜子中看见自己对自己的爱怜,才觉得自己没有一丝一毫的神性;像昼神幸郎这种向外发散着爱怜的人,才会觉得能做到把情感全部收拢向内不是懦弱,而是种强大。
但我本就没奢望镜里人和我一模一样。我关心的是:“你不是说,不会和神相触碰、接吻……”
“我说的是‘不会吧’。话可没说死。”
“贡品,在哪里?”
“饶了我吧。我都上供多少次了。”
显而易见的荤段子。我恼了。昼神幸郎反而开心了:“反正你不会无视我了,现在。”
“这可不一定。哪天你交到女朋友了,我会装陌生人的。”
“如果是你呢?”
——如果那个女朋友是你呢?
因为我见过昼神幸郎的眼睛,我知道它不是黑色的,即便如今没有灯光,我也知道它不是混沌、不是黑暗。不可捉摸的赫拉克利特的长河,此时此刻,我应该迈进去吗?
我们的开端就是错误,脱轨,偏斜。回到正轨的样子?我难以想象。
什么是镜子?注视眼睛的眼睛。什么是影子?身体的另一个身体。我回避了我的镜子、我的影子,不敢直视:“要考医学部的人,想什么谈恋爱。”
长野县多山,山里的夜静得可怕。我不在山上。我在山上吗?会有月亮吗?月光是否不再如水,隔着大雾朦胧不清,徘徊许久,最终在无奈的叹息声里飘散。
昼神幸郎:“真无情啊。”
我:“我还不想人生玩蛋。”
因为我闭上了眼睛,他那只手也不必忍受睫毛的骚扰,可以彻底向下盖住了:“你很努力学习了。会有好结果的。”
这回是昼神幸郎避重就轻了。
入殓师用手帮逝者合眼时,部分人只能合上一阵子,过一会儿自然会睁开。至于我,我现在还活着,于是直到入睡也一直没睁开,认下了和他一起装糊涂。
“这句话也送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