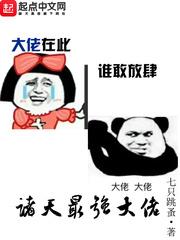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伽蓝国是怎么灭亡的 > 第31章(第1页)
第31章(第1页)
>
母亲那边传晚饭,听说白清明也在,便让独孤金金叫他一起用饭。可是她还未进门就听他絮叨,竟是在交代后事。她愣在门口,突然狂风大作,吹得她睁不开眼。屋里的白清明也被吹得用袖子掩住脸,再放下时,袖子已经被揪住,躺得好好的人圆睁着眼,面容有些扭曲。
白清明也瞪圆了眼睛,有些尴尬似的:“刚才那些话你听去多少?”
“不好意思,一字不漏。”
“你醒了,那我就回锦棺坊了。”
“回去等死?”
“在这里也是等死。”
柳非银猛地坐起来,想起夙墨说的话,若是想治好白清明,只能用凤毛麟角孔雀翎。而原本白清明有只麒麟角的,还让他还回去了,如今,也只能等死……吗?在外人看起来比较痛苦的,反而是躺在床上的这个。白清明也不忍看他难过,别过头在屋子里找了一圈:“我在这屋子周围布了结界,刚刚好像进来什么东西,跟你同时回来的么?”
正寻着,耳后吹来轻微的风。是熟悉的气息,带着点微苦的松香。只觉得眼前一湿,被滑腻腻的狼舌舔了眼睛,视野顿时清亮起来,什么都能看着了。柳非银叫了声“狼兄,你少动手……动嘴啊”也揉了揉眼,整座屋子被雪狼占了大多半,他就卧在白清明旁边,居高临下。
记忆里,白清明只有两三次见过他的原形,都是月圆时。而这次不同,他像座小山般那么大,皮毛上布满了彼岸花的花纹,带着不祥的气息。
“师兄,你来了。”
“嗯,本应该早来两天的,半路去看了一趟老朋友,耽搁了。”那雪狼不冷不热地说,“月圆之夜我化不成人形,你将就一下,现在连鬼魂妖怪都看不见了吗?”
“嗯。”
“你身上已有腐败的气息了。”
“嗯。”
柳非银彻底怔了,没少听白清明叨念他这个师兄,除了每隔段日子就从瑶仙岛来的书信,他对这个师兄的了解近乎于零。面前这头威风凛凛的雪狼妖,他是个如假包换的封魂师,他叫白寒露。
白寒露甩了甩尾巴,冷淡的口气透着愉悦:“那就按我们说好的,我治好他肉身上的毒,你死前把封魂师血脉完全过渡给我。”白清明答应得爽快:“好!”
床上的人眼睛瞪得比鸡蛋还大,他竟说好?他竟说好!他随随便便就把他柳非银大爷的死活给安排下了,一点都没问过他的意见!谁说好,就让谁好去!柳非银气得双眼冒火,身子躺了几天尚且用不上力气,一翻身就从床上滚下来:“白清明!我问候你爷爷!你敢!”
到了如今,他还有什么不敢的?
事到如今已经很简单,肉身上的毒对于身为封魂师的白寒露来说,根本就是手到擒来的事。白清明不理他,朝着门外喊:“金金,你进来按住他,我还要留些力气应付今晚的事。”
独孤金金只能摸摸鼻子走进门,在屋子里找了一圈,便伸手胡乱地摸索,突然手下触摸到温暖顺滑的毛,虽然看不见,却是实实在在站在那里的。她诡秘一笑:“白寒露是吗?我叫独孤金金,你可记住了。”
「你瞧瞧你身上那是什么?曼陀地狱?!你以为你去了曼陀地狱烙上了受过刑的印记,你就是干净的了吗?」
很快月亮便爬上树梢,银色的满月周围泛着淡淡的血色,夜越深,那血色便泛滥得越浓。
白寒露背着白清明回到锦棺坊。他瞧着朱红的大门,屋子里被他折腾得金碧辉煌的,连衣裳都是锦绣团花,可见这男人日子过得多么奢靡又庸俗。他对这个师弟没什么好感,自然看他什么都不顺眼。
白清明见他连说话都懒,便笑着说:“看你也不愿意在这里,先把这封魂师的血给你渡了,而后你便跟那头黑狼妖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我这些日子撑得也够辛苦了,也撑不下去了。”
这笑容里带着点淡淡的哀伤,不知为何,这种笑容竟让白寒露觉得有些刺眼。好似在哪里见过似的。
也许这么多年书信往来,他虽然不喜欢这个师弟,但是对他也是没什么恶感的。而且他为了救那人竟然撑了那么久,好像性子也挺喜人的。眼看着那人已经准备好了道具,连串口气都觉得费劲儿,竟破天荒地觉得有些难过。
“……我还答应过你将鬼牙送进曼陀地狱,等我送进去了,你再渡给我,省得说我诳你的。”
“嘿嘿,师兄你还是老样子啊,跟谁都清清楚楚的。”
雪狼琥珀色的眸子稍微柔和了些:“我是生意人,总不会让客人吃亏的。”白清明点头,做生意的确如此才能财源广进,这些年师兄的确也把他的醉梦轩做出了名堂。
今夜真的很美,红色月圆之夜鬼门大开,群鬼们欢笑着跑出来,边唱边跳,粼粼鬼火俏生生地浮在半空中像萤火虫。而小妖怪们却是不敢出门的,今夜是狼族的饕餮之夜。
巨大的雪狼驮着他飞过城池上空,风临城伏龙镇外有座山,而此时传来幽幽的狼嚎声。白清明摸了摸师兄脊背上的彼岸花的花纹,这花纹来得太奇怪,以前从没见过的。只是师兄是有个性的师兄,他想说的话就唧唧喳喳个没完,不想说,你就是问,他也会觉得你是恼人的苍蝇。
雪狼妖的气息吓得一众灰狼们卧在山头上双爪捂着头呜呜叫,山上离那红色月亮似乎更近了些。白寒露寻了块平滑的石面让白清明坐下,自己也卧在他身边,静默地看着山下的镇子里的喧闹的群鬼。这会儿白清明心里十分满意,在离世之前有师兄陪着他一起看过群鬼夜行,总算是圆满的。
鬼牙是循着白寒露的气味来的,他的原形比白寒露小了很多,不过是比普通的狼大些,那狠戾之气却有过之而不及。两匹狼互相审视了一会儿,还是鬼牙先开口:“对了,我现在应该叫你白寒露了。这些年你倒是过得挺逍遥嘛,早就忘记了当初我们在狼窝饿得嗷嗷叫的时候了?”
白寒露一贯冷淡的态度:“是的,我忘了,我有一段时间的确是忘了。”
“你根本就是忘记了!”鬼牙大笑起来,“你瞧瞧你身上那是什么?曼陀地狱?!你以为你去了曼陀地狱烙上了受过刑的印记,你就是干净的了吗?不会的!你不会被原谅的!姑娘她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
是啊,姑娘。
他觉得这短短的几十年,却像过了几辈子,而姑娘也死了几辈子。
白清明把手搭在师兄的长尾上,不轻不重地顺着,以前小时候,师兄难受的时候他便这么顺着他,只是他忘记了。师兄的记性的确是不怎么好。这么折腾了一路,白清明胸前的伤口又裂开了,血水止不住,他也懒得去擦,笑着问:“看来在下成为这副样子,都是因为你口中的这个姑娘,兄台何不说个清楚,也好让在下做个明白鬼啊。”
鬼牙盯着他,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黄土埋到了脖子上,还能笑得这么欢畅。他说:“如果这是你临死前的愿望,那我就讲给你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