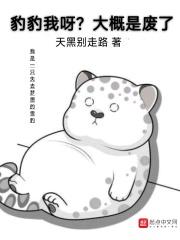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逆贼敢尔 > 第158章(第1页)
第158章(第1页)
>
白钰顿了顿,又道:“东州沦陷后,耗尽国库的中都朝廷自是拿不出出兵的粮饷,只好向东贼绥靖怀柔。如果野王能率军东攻,便是这半百年间大胤的首次对外战争,不管成败与否,都将振奋人心。只要天下的百姓能看到野王光复东州的决心,野王便是得到了这天下的民心,有了天下百姓的支持,野王何愁大业不成?白钰这就回去研究此战,三日内为野王献上东攻的良策。”白钰拱手便要告退。
萧野在身后叫住了他,“等收复了东州,先生晚上便不会再做噩梦了。”
白钰转身恍惚着抬眸看向萧野,眼神炽热,泪眼涟涟,道:“野王攻东州,可是为了白钰?”
萧野没有否认,他知道光复故土一直是白钰的执愿。平素白钰不提,一般人是不能在他的脸上察觉到什么的,但那日的鸿门宴上,当萧野提出要收复东州时,白钰眼神里流露出的欣喜若狂,是他至今都难以忘却的眼神,渴望,欣喜,炽热……
自从白钰搬过来跟他同床共寝,每到午夜,白钰便会头冒冷汗,眼角流泪,任萧野怎样呼唤,也叫他不醒,这梦魇如癔症一般,灼得白钰胸口生疼。萧野询问白启才得知,白钰自从东州沦陷独自逃生后,便患上了这心疾,心病还需心药医,自那后,萧野便下定了要光复东州的决心。
晚膳后,白钰将父亲将他送出城时给他的护命短刃从锦盒中取了出来,回想着他遇到萧野之前的经历:这把短刃杀了送他出城后想轻薄他的东贼兵;杀了流亡津州途中,抢他吃食的流民乞丐;杀了将他绑到山匪窝里,想侮辱他的山贼匪首……
这把短刃如他的护身符一般,每每救他死里逃生,白父是明智的,在乱世里存活,从来都不是靠求神拜佛,永远能相信的,只有自己和自己手里的刀。现在,他多了一样愿相信的,萧野!
见萧野进屋,他自若地将短刃收入锦盒,笑着向萧野迎了过去。
“野王因校场修建累了一日,阿钰伺候野王早些休息吧。”白钰伸手便要为萧野宽衣解带,萧野抓住白钰的手,一弯腰,将白钰打横抱起,向里间的温泉池走去。
白钰有些羞涩,眼神撇过旁边,对萧野道:“野王要沐浴,阿钰还是去外面等候吧。”
“先生在回避什么?”
白钰抿唇不答,自他搬入萧野的寝房,他们除了每日睡在一处,别的便再也没有做过。
白钰不主动,萧野便也不动。两人默契地暗自较着劲,赌谁先主动靠向对方,尽管这种举动幼稚非常。
白钰装作无辜,拿乔道:“野王今日怎的兴致高,邀白钰同沐了?”
萧野将白钰放下,轻咳了一声,滚了滚喉咙,道:“先生今日知道了本王东攻的缘由,心里难道就没有一丝的感动?”
白钰听到萧野的话,遽然间捧腹大笑,道:“想不到高高在上的野王,竟然为了床笫之欢,竟有如此面貌?”
看到白钰的嘲笑,萧野也脸红着挂不住了面子,直接褪衣入了水。
这些天的夜里,萧野躺在床榻之外,白钰则躺在床榻的里侧。白钰睡觉好翻身,但每次翻身都若有似无地触碰到萧野,但脸上却不见半点波澜。如果说白皓宇是一支倾世白莲,清冷,美丽,惹人心仪;那白钰便像一只绝色白狐,孤傲,狡黠,充满诱惑。
白皓宇是萧野的白月光,那白钰便是萧野的朱砂痣,一人陪了他的前半生,一人伴过他的后半世。
白钰见萧野下了池,自己则蹲在池边用水勺给萧野撩水,白钰褪去外衣,穿着白色的亵衣也迈入了温泉池中。
白钰向萧野伏身过来,眼眸含情,勾唇笑道:“春寒共浴白莲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野王,白钰伺候您沐浴。”
翌日。
萧野闻鸡起床,发现白钰已不在床榻,他问过白启后得知白钰半夜便起床挑灯去了书房。
萧野穿戴整齐,抬脚进了书房。
白钰趴伏于案台之上,微阖着眼,枕着东州的舆图,通宵达旦,脸侧前还放着一只燃尽的白烛。
白钰睡的浅,察觉到眼前的光亮被遮,便睁开了眼睛,抬眸看向萧野,微微一笑,问道:“野王昨日可睡的香甜?白钰服侍的,可还满意?”
萧野看着淫笑非常的白钰,心里有点儿莫名不适,道:“先生饱读诗书,这种敦伦情事怎可轻易出口?”
白钰酸痛着身子,有些不悦,这里又没外人,装什么正经,也不知昨晚是谁自己都说不要了,还不肯停下。白钰眼睛一撇,道:“野王是觉得白钰白日宣淫,放荡不堪,有辱斯文,不知廉耻。”白钰抬眼再看萧野,傲娇道:“野王是正人君子,白钰是风流浪子,是白钰夜夜缠磨着野王,一切羞耻,一切污秽,全由白钰一人承担。野王现在是津州之主,将来会是天下共主,新朝明君,而白钰只是一介布衣,商人之后,自知德行浅薄,配不得野王。”
“先生为何要这样说?我萧野从未将先生视为低贱之人,更不介意先生的出身。”
白钰听萧野如此说,试着问道:“那将来,野王荣登大宝之时,野王打算如何处置白钰?”
萧野听闻无言,在白钰问他之前,他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白钰见萧野不言,便是知道了答案,道:“野王不必担忧,到那时,白钰自会隐退于市,白钰还要重振白家的产业呢。”
“先生,到那时,我会以江山为聘,十里红妆来迎娶先生,先生可愿嫁于萧野,做这天下主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