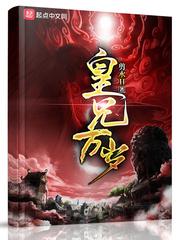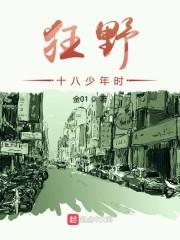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六爻在线排盘 > 第76章 生机断绝处剑成(第2页)
第76章 生机断绝处剑成(第2页)
吴长天愣了愣。
“因为他在十来岁的时候,中了你们天衍处前辈周涵正的一封画魂,你可知道什么叫做因果报应?”
程潜声音很低,仿佛面对这一群人,他连说话的力气都不肯多费,“大人方才说什么?你道中人?”
他话音突然转冷,霜刃“呛啷”一声出鞘,一道海潮似的剑气凌空斩过,在地上划了一道几丈长的弧线,站得近的几个天衍处修士全给他这一剑扫了出去,一时间人仰马翻好不狼狈。
程潜的目光比剑光还冷上三分:“带着你的狗滚,敢踏入此线者,就等着下辈子投个好胎吧。”
就在这时,山庄的门“吱呀”一声从里面打开,水坑走出来,装模作样得仿佛像个大家闺秀,冲外面的众人一敛衽:“三师兄,掌门师兄让你不要胡闹,快些进来——诸位,我们掌门近日闭关,不见外客,请诸位客人见谅啦,自便。”
听得出水坑也不习惯这么说话,她本是个漫山遍野扎着翅膀乱飞的野丫头,叫她去学人们那虚以委蛇的一套,实在是有些勉强,程潜心里微微转念,不由得暗叹口气。
门派凋敝,却偏偏总在风口浪尖上。
他冲水坑打了个眼色,留下了一个倨傲的背影,抬手将扶摇山庄的门封上,大步往里走去。
水坑连忙大大地松了口气,小跑着追了上来,喋喋不休道:“小师兄,你怎么回来得这么快?找到让大师兄醒过来的办法了吗?我跟你说,他眉间的心魔印前些日子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短了一些,你说这是好兆头吗?”
程潜简单地点了个头,说道:“嗯,我要闭关百日左右,最好别让那些人来打扰。”
“好的,我去和二师兄说,反正他鬼点子多,”水坑连连点头,忽然,又仿佛想起什么似的说道,“对啦,小师兄,你不知道,大师兄好像能听得见我们对他说话呢!”
程潜的脚步蓦地一顿。
水坑乐颠颠地接着说道:“你说我多去找他聊天会不会……咦,小师兄,你怎么了?”
程潜不由得想起他和唐轸在严争鸣床前肆无忌惮的谈话,莫名地有些心虚,他避开水坑的目光,伸手掩口,欲盖弥彰地干咳了一声:“没什么。”
同时,程潜心里默默地回顾片刻,他们家大师兄从小就不学无术,被师父念经念得据说看见字就犯困,除了本门经书与心法,没见他碰过别的书本,应该……应该不会多想什么吧?
在水坑诧异的目光下,这方才还拿着霜刃大杀四方的人突然面露尴尬,脚下如抹油,匆忙跑了。
第二天,扶摇山庄仿佛被头天纠缠不休的天衍处激怒了,整个山庄换了防御阵法,原本只是温和的防御阵中似乎有某种凶戾之物加入了阵眼,阵法顿时改天换日,隐隐地环绕着一圈逼人的杀气,肆无忌惮地四散出来,分明是要拒人于千里之外。
山庄里,外院中的小厮已经被清理出去了,院中霜刃高悬,正是此阵的阵眼。
李筠不由得擦了把汗,拱手对身侧的唐轸道:“全赖唐兄指点,多谢了。”
“李道友不必多礼,我只不过是动动嘴皮子而已,”唐轸说话间,目光从霜刃那雪亮的剑身上掠过,感慨万千地说道,“‘不得好死’之剑,大约也只有令师弟这样的人,才差遣得动这种不世出的凶器。”
李筠负手叹道:“我总担心他太过偏执强硬,过刚易折。”
唐轸笑道:“李道友也太多虑了些,修士与天争命,不执着的人大多走不长,他这样不到最后一刻都不肯放弃的人,岂不心性正佳?”
李筠眉宇间忧色更甚,说道:“修行什么的倒是其次,只是我担心……万一事与愿违,师兄他出点什么事,小潜会不会……”
唐轸听到这里,眉梢微微一抬。
会怎样?
然而李筠却又将下文吞了回去。
李筠好像才意识到身边的人是唐轸一样,连忙显得有些魂不守舍地抱拳道:“唉,这话一说就多,都是我们门派中鸡毛蒜皮的小事,便不拿来搅扰唐兄了。”
唐轸道:“那倒无妨,只是程小道友一声不吭地突然要闭关,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哎,李道友,你说他总不会异想天开地打算自己造一把剑吧?万一他不成功,严掌门的身体恐怕也撑不了多久了,到时候李道友打算怎么办呢?”
李筠闻言,心里好像没有一点成算似的,在唐轸面前呈现出了一个真正的窝囊废,脸上写满了真正的六神无主,苦笑道:“这我真不知道……不瞒唐兄,掌门师兄就是我们的主心骨,现在主心骨倒下了,我们也就……唉,真是让唐兄见笑了。”
唐轸盯着他的脸看了片刻,只觉扶摇派众人中,若当真动起手来,这李筠可谓是最软的一个柿子,偏偏此人心眼多得好像蜂窝,又狡诈又多疑,两人你来我往聊了半晌,谁也没有试探出对方半点真话。
此时,回到竹林小清安居中闭关的程潜手中正拿着一把平平无奇的木剑,不过三尺长,轻得要命,木头纹路平和优美,看不出一点杀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