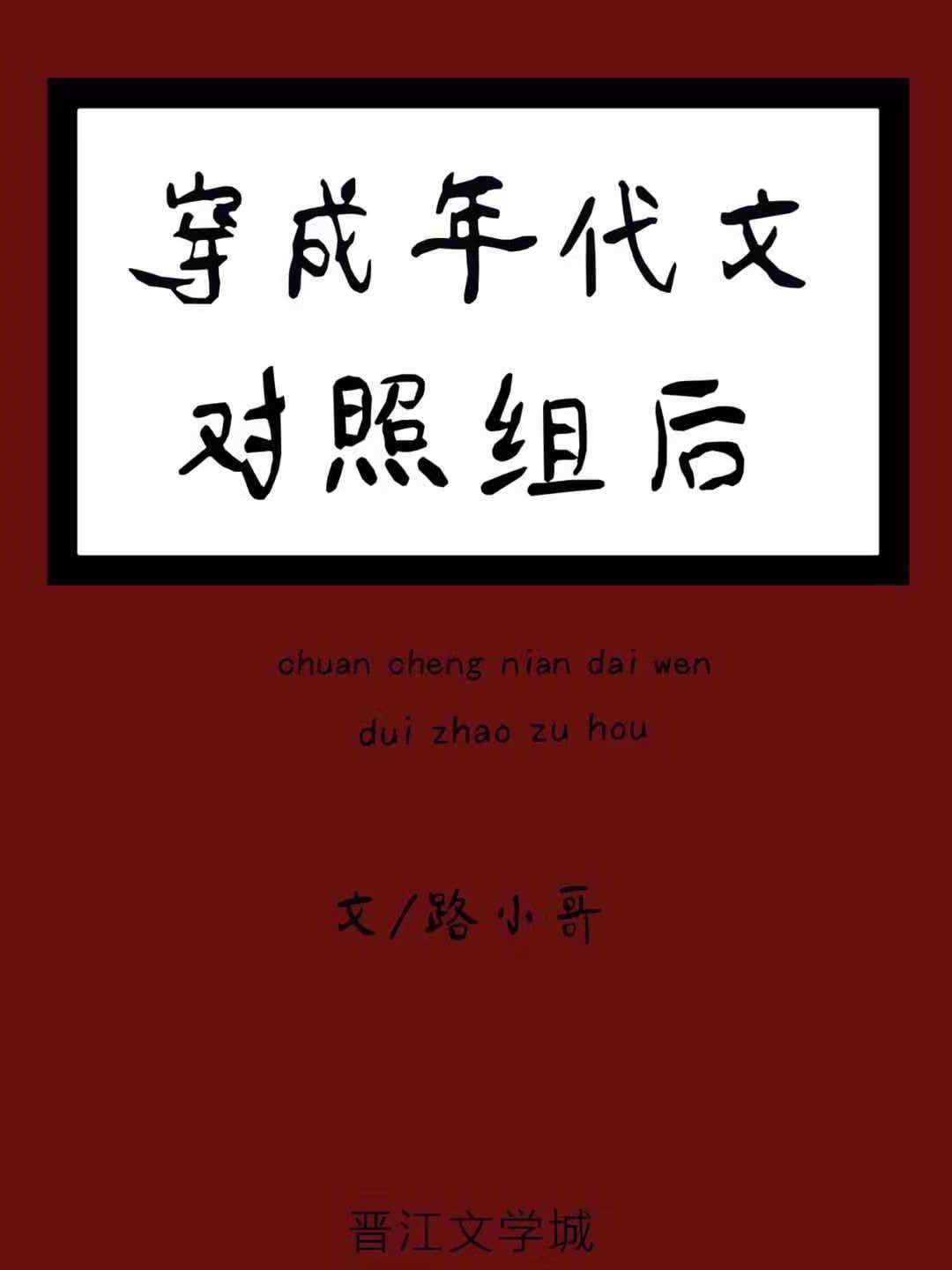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重生之临终遗言全文阅读 > 第14章(第2页)
第14章(第2页)
挂了电话,季童很顺利在电脑上找到个监控录像的临时文件夹,打开找出晚上那个时间段的记录。
这段记录清晰的像用高清专业摄像机录的一样,只是受限于角度是从上向下拍,并不能完整地看清男生的正面全脸。
在画面里,他确认了门上贴着的A4打印纸之后似乎很高兴,但是完全没有靠近门缝,反而是摆出一个侧耳听什么的姿势。
然后就靠着墙随便坐下发了几分钟呆,镜头里只能看到他漆黑的发顶和露出的尖下颌,如果不是画面还在记录,季童简直以为这个人僵成雕塑了。
持续近十分钟的时间里,这孩子完全没动,然后有什么东西在画面中一闪反了一下光。
季童推回画面,一帧一帧看,最后有些惊讶地钉在某张图上。闪了一下的,是一滴液体,跌落下来的……
这孩子在哭!
然后画面中的男生很快站起来,理了一下抱的有些散的一叠文件,按了按眼角,步速很稳定的离开了。
接着再去看大楼监控,他径直下了楼梯出实验楼,一路向宿舍区过去了。
季童按了按额头,回忆起早晨在花廊附近撞到他的时候,自己看到的好像也是一双发红到泪汪汪的眼睛,当时还以为是受伤。
在回放刚才那几分钟画面,一个晚上独自跑到空旷的实验楼里发呆的男生,刚才那种坐着不动哭了一下然后又走开的姿态,莫名让胸口闷闷的。
有些熟悉……
记忆深处,好几年前的时候,嘉木和家里摊牌闹翻,被赶出来。自己打工累极,安慰了几句在他反复说没事儿之后就睡了。结果半夜醒来,发现裴嘉木抱膝坐在飘窗上,溶溶的月色下脸颊上有一行银亮的水迹。
季童记得当时自己心疼的不行,又爬起来安慰,裴嘉木简直一秒变脸,抹掉眼泪之后笑的特别灿烂,坦诚说只是难过小时候在那栋房子里和爷爷的美好记忆再没有了。接着他还淡定地讲了一通什么人都要向前看的废话,反怪自己太过大惊小怪,信誓旦旦说没什么可担心的。
那个晚上之后,果然,再也没见过裴嘉木因为家里的事情表露出难过伤心的情绪,他总是乐观的,什么都能解决。连最后离开,也记得留了一个笑脸……
晃了晃脑袋,季童关上电脑重新躺回行军床上,嘉木已经不在了,不能继续沉浸在回忆里,要听他的话好好过日子开始新生活。
数百米外的宿舍楼里,对大多数人来说,又是一个闷热的夏夜。
裴佳木被舍友起来冲凉水的声音吵醒,摸了摸自己凉丝丝的胳膊,好吧,虚弱畏寒的体质这会儿是好的,全宿舍都热的恨不得躺地面上,只有他自己,还在肚子上搭了条毛巾被。
迷迷糊糊重新睡过去,夜里忽然做了乱七八糟的梦,一望无际的麦浪,田字格一样的田间小路,道路两边的梗上种着一些高高矮矮的树。跑在乡间小路上的大黄狗,摇摇摆摆高昂着头的鹅群,四处刨食儿的鸡,隐约尖利的吵闹声。明明没有看到什么,可是意识里就是能感觉到鼻尖萦绕着牲畜粪便发酵的臭味儿。
一幅幅破碎不连贯的图画,都是裴佳木上辈子只有从影视作品里才能看到的东西。
早晨被凉丝丝的晨风吹醒的时候,在床上愣了好一会儿神,屋里还有舍友轻微的小呼噜,裴佳木轻轻抬起右手按在左胸。
这种情况,是身体原来的主人想赶我走吗?还是仅仅是生物学上的大脑里的残留记忆?!
一周以来的好心情变的有些沮丧,莫名醒来的倒霉情形再次退的无比的远,会不会再莫名失去直觉,成为游魂一样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