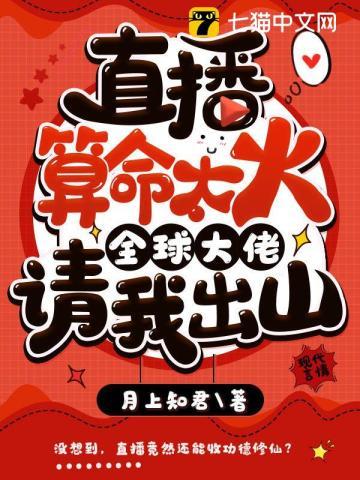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晴朗的天空什么什么的 > 第23章(第1页)
第23章(第1页)
>
“嘿,他还真够义气!”阿童木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在三三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
“嗯,他当然是。”
“那你干吗不承认你喜欢他?”
“我没有。干吗非得要喜欢他?”
“是吴晓芸做的,那个娃娃。”阿童木沉默了片刻以后说,“本来不想告诉你的。”
“啊?”三三的心死命沉了一下。
“谁叫你非要头上长角呢?你又想要头上长角又想要大家都喜欢你,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早就知道了。所以连我爸爸现在都讨厌我,他说我的脑袋后面天生长着反骨。你摸摸你脑袋后面,你睡觉的时候搁在硬床上是不是也脑袋疼?你干吗非要在乎这些狗屁事情,还有那些狗屁女同学?”说完阿童木就回头张望了一下空荡荡的操场,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黑板报上那张刺眼的白色布告纸撕下来一大片,单剩下被糨糊粘得死死的一小块纸片,上面可怜巴巴地印着校长的名字和一个印泥染到外面去的正红色公章。
她眼巴巴地看着阿童木又把那一大片纸撕成了碎纸条扔在地上,然后对着她说:“嘿,笨蛋,还傻站着干吗?我不怕,但是你要是被老师看到就死了。快跑啊!”
笨蛋,笨蛋,快跑啊!
10.
吴晓芸在天气渐渐变暖前突然转学了,但是这跟她塞在三三书桌里面的那个袜子娃娃没有关系。三三压根就没有想过要报复她。阿童木再次在她的课桌里面撒了一泡尿,还把她的两本教科书在教室门口用火柴点了烧了。那堆纸灰外面他拿黄色的粉笔画了个圈,就好像是家里死人时烧的锡箔一样。三三那天生病没有去学校,所以没有看到她嚎啕大哭的样子。而这一切只是让更多的人开始讨厌三三,班级里所有的女生都不再跟三三说话。中午去食堂里取妈妈给她准备的饭盒时,她总是被男生们故意挤在队伍的最最后面,轮到她的时候所有人的饭盒都已经拿光了,只剩下她的那个,常常已经被掀开盖子碰翻了。妈妈为她准备的红烧大排或者两只炸鸡翅会被扔在旁边的水沟里,只留下被蒸得发软的白饭和几根完全蔫掉的青菜。三三不知道是谁做的,好像他们都心照不宣而又习惯性地做着这些,比如说把她铅笔盒里的铅笔都折断,在她的椅子上粘嚼过的口香糖。她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这些。她自己从练习本上撕下纸来把口香糖弄掉,或者吃两口寡淡无味的白饭也不是很大的问题。阿童木不知道这些,林越远也不知道,或许很多年以后她可以告诉他们这些就当是说一个笑话,但是那时她像个死硬派的小女孩一样把一切都就着白饭默默地吞下肚子。可不管怎么样,她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要报复吴晓芸。
吴晓芸有一天突然就不再来学校了,而前一天放学后三三还看到她坐在数学老师的办公室里面写作业。她总是可以在老师办公室里写作业,因为她妈妈常常因为工作要很晚才能来接她,有的时候她还会帮数学老师批改测验卷上面的选择题和填空题,填写成绩单。三三那些糟糕的成绩单大部分都是吴晓芸放学以后在办公室里面填的,她交替使用红色和蓝色的圆珠笔,一板一眼很当回事。前一天放学时三三还被数学老师叫到办公室去,她知道是因为有一张数学测验卷没有签名。那张试卷被她折得很小胡乱塞在书包里面。但是走到楼梯的拐角处时她还是不放心地把那张破烂纸翻出来,掖在了皮带和肚子间的裤子边上,再用衣服盖好,然后她可以撒谎说把卷子落在家里面了。他们可以随便翻她的书包但总不会搜她的身。当三三惊魂未定地撒着弥天大谎的时候,吴晓芸趴在旁边的玻璃台面办公桌上写作业,旁边放着一包瓜子和一包大概是午饭时剩下的豆奶。那天还很冷,但是她在厚厚羊毛袜的外面穿了毛线的编织裙。她抬头看了三三一眼,然后迅速又嫌恶般地把脸别过去,所以三三脸上僵着半个古怪的笑容。此刻她嫉妒极了吴晓芸,嫉妒她可以在冬天的时候穿裙子,嫉妒她总是第一个知道所有人数学测验的成绩,嫉妒她在老师办公室里旁若无人地嗑着瓜子竟然还显得那么好看。妈妈总是说女孩子冬天穿裙子的话,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关节会疼得在地上打滚,可是谁在乎年纪大了以后的事情?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女孩来说,年纪变大简直是永远都不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第二天三三满怀心事地等待第二节数学课的到来。她依然没有把那张该死的试卷拿给爸爸签名。她的手伸在桌肚里捏着那张咸菜般的卷子,手心里全都是汗。但是,那个满脸粉刺和脓包的数学老师没有出现。她想他大约是生病了或者是到外校开会去了。过去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显然急匆匆跑进来的班主任带来了一个更好的消息:数学老师不会再来学校里上课了,他们从明天开始会有一个代课的数学老师直到毕业考试。于是她沉浸在不用再见到这个讨厌的数学老师的喜悦中。她讨厌他,因为他很少给她好脸色看。她并不是不会做那些题目,但是她是个粗枝大叶的女生,她不在乎那些约等号或者是那些竖的计算式只是因为她很粗心,他却真的把她当成一个会在数学测验时怕得尿裤子的笨蛋。他一定是这样跟办公室里面其他老师讲的,他根本不知道原因。但是现在再也不用看到他了,桌肚里的那张数学测验卷再也不用签名了,她可以把它撕碎了扔到抽水马桶里面冲掉。这个消息简直好得过分了,所以她忽视了班主任面孔上尴尬为难的的神情,还有班级里那些碎嘴的女生窃窃私语的古怪气氛。直到放学后大家都在说吴晓芸也转学了,她才突然感到很疑惑,仿佛她总是那个被蒙在鼓里最后才知道真相的人。
在女厕所的隔间里面,两个隔壁班的女生在说:“他被门卫老头抓住的时候,她的裙子褪到膝盖上了。”她想象得出她们捂着嘴吃惊的神态,大概还彼此掐了对方的胳膊才忍住尖叫,“天哪,太可怕了!”
之后学校紧急召开了一个家长会。有史以来第一次,爸爸回家以后没有说起她成绩的事情,也没有发火,却是极其担心又极其温柔地用手摸着三三的头发问:“你们的数学老师有没有叫你坐在他的大腿上写作业?”
三三不知道他们说的数学老师或者吴晓芸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没有办法把整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只是害怕地想那一定是一件非常非常坏的事情。那时候她根本就不知道男人和女人是怎么一回事,她以为只要亲吻就会变成大肚子。有一年暑假,表哥住在她家里面,他常常游完泳回来以后就直接用嘴对着茶壶喝水,所以整年的夏天三三都坚持不肯碰那个茶壶里面的水,总是等妈妈重新烧完开水以后用自己的杯子给自己凉白开水。大人们只以为这是她古怪的小女孩的恶癖,或许是跟弄堂里哪个女生学来的鬼鬼怪怪的事情,却不知道她是害怕自己变成大肚子。直到很久以后她才突然想明白了吴晓芸和粉刺数学老师之间的事情,但那时她已经是一个中学生,每天放学后都要挤三站路的公交车回家。有一天她被挤在香蕉座旁边的狭窄缝隙里,拉不到扶手,只能把书包紧紧地抱在胸口左右勉强维持着平衡。那天也是冬天刚刚过去而春天却未到来的尴尬季节,有一只生着老茧的男人的手突然从她校服上装的腰间插进来。她浑身哆嗦了一下是因为那只手很冷,而且它狡猾又灵活地穿过了毛衣和棉毛衫停在了她的后腰一大片被迫裸露出来的皮肤上。她吓得不敢动弹,想要呼喊却看到周围都是冷漠的乘客,所以光是张着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喉咙口却好像被火烧起来似的,只能够绷紧身体,连脚尖都绷紧了。可是那只手却毫不善罢甘休地往她的裤腰伸去。她束着很紧的皮带,所以它犹豫了片刻便用两根粗大的手指用力向皮带扣探去。老茧和指甲划过她的肚子,弄疼了她,她轻轻惊呼了一声。这时候正好车子到站,她拼命地从人缝里面往外面挤,累赘的书包从很多人的肩膀和腰后压过,大概还钩坏了哪个女人的毛衣,因为直到下车后她才看到拉链上挂着一截毛线。但是她顾不得那么多了,在车门关闭前的最后一刻跳下了那辆车,心脏乱跳,明明很冷刘海却被汗弄湿了紧紧贴在额头上。走在路上,她不停地回头张望,担心那只手有没有跟着她一起跳下车来。她稀里糊涂地沿着漫长的北京西路走,跌跌撞撞,突然想起了吴晓芸来,还想起数学老师唯一一次让她坐在他的膝盖上,在她的耳朵旁边极其温柔地说:“不要害怕,坐在我的腿上,不要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