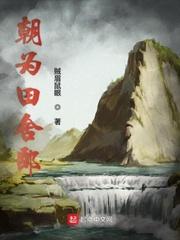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女扮男装龙傲天漫画 > 138 第一百三十八章(第2页)
138 第一百三十八章(第2页)
“告诉他做甚?指不定回头拿这个做把柄将你我三人一齐赶回老家!”矮子最先反驳。
反驳后几人皆默不作声,过了片刻,光头士兵嘶了一声道,“他可是陛下派来的人,真的不会出什么事吗?”
“萧子客出事儿,不是正合咱们仨的愿吗?”矮子再次声。
此声过后,三人又是一阵沉默。
“不然看在萧老将军的份上——”光头士兵迟疑着开口。
他只说了半句,另外二人却会意地互相注视着对方,刹那后,原先几人站处已经空无一物,三人抬腿向外行去。
“当真直接进去?”铁向褴与万俟已行至州府外,至今铁向褴对萧小河的命令仍感不决。
“咱们这样进去,能查出个什么?总不能直接问那姓任的为何栽赃将军。”在铁向褴的设想中,应当是身席夜行服,如羽卫军一般日日潜伏探听,现端倪趁此追查,再将贪官污吏们一网打尽,而不是如今这般亮明身份,大摇大摆地走进去。
况且从马主人口中得知,与刚上任半年的巡抚不同,任缵祖在蕲州已任二十余年,其根基至深,无论是各县官僚还是各大商贾,都与任缵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说是一方土皇帝也不足为过。
此人曾是卫少焉门生,素有笑面夜叉之名,在百姓口中恶名昭著,却无人敢拿他如何。
而且任缵祖身为一州之长,手中还拿着兵,寻常军队一律由他管控,只是萧小河的伐燕之军有些特殊罢了。
蕲州天高皇帝远,这样的人,想在他的地盘撼动他,对萧小河来说都绝非易事。
也难怪马主人那偌大家业会付之一炬。
据马主人所说,自从频频加税后,越多的商户联名致书顶抗,本以为法不责众,却未曾想任缵祖会一家一家计较过来。
有些怕事儿的,只得认倒霉,乖乖交着罚税,继续苟延残喘,有些强硬的,如马主人之流,则去寻巡抚,敲了鸣冤鼓,最后结局亦是凄楚悲切。
铁向褴听后十足触动,心中又生起一鼓无力之感莫说这些百姓了,倘若是他,让他瘫上这事儿,他也不知道如何做。
整个蕲州皆是任缵祖的领地,逃也逃不掉,消息也递不出去,除了认栽只得玉石俱碎,也未见能如愿。
将军到底想如何做?
铁向褴猜不到,只知晓如若硬碰硬的话,怕是会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萧小河绝不会如此。
“你敢不听将军的话吗?”万俟听了一万遍这个问题,早就厌烦,没好气地责问道。
“不,不敢。”铁向褴摇摇头。
“既然不敢,你再问这些有何用?还不如快些进去!”万俟道。铁向褴点点头,率先走到了州府前,还未等他对门口守卫表明身份,就见为的二人退后半步,顺从地俯身抱拳行礼:“铁副将!”
铁向褴被吓了一跳,他很快反应过来,不动声色地点点头:“不用多礼。”
“任大人可在?”铁向褴示意万俟跟上,尽量克制住惊诧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