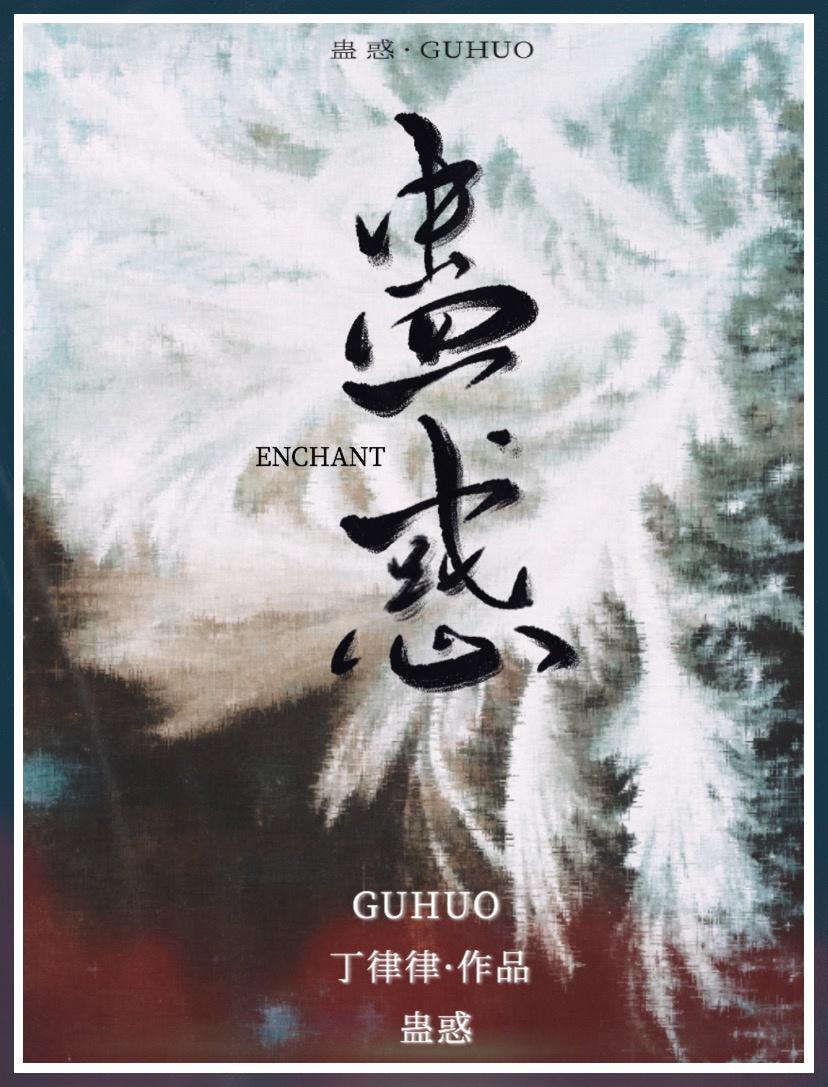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宋末崛起 聚合中文网 > 第七十二章赵頊的愤怒(第1页)
第七十二章赵頊的愤怒(第1页)
“三郎,你怎的这般糊涂,武职怎地不好,看看我们的寨主,在寨子里就是土皇帝,谁家有事不是请他做主,年节收到的礼金无数,耕种的时候随意让军卒给他家耕种,秋收时候军卒最先要去给他家收地,唉,”
秦伯义感概了一下寨主无法无天的小日子,对失去官身极为的失望。
“三郎,此番皇上赏赐的是什么官职,”
秦庆问道。
“官阶是西头供奉官,差遣是保捷军厢都虞候,”
秦延随意道。
“什么,”
秦伯义又激动了,没法不激动啊,
“塞门寨的寨主也不过就是厢都虞候而已啊,于寨主可是从军二十余年,不过熬到了这个差遣,你可是只有两月有余而已,唉,可惜了,可惜啊,”
秦伯义痛心疾首,厢都虞候啊,西头供奉官啊,这可是妥妥的中阶军将了好嘛,虽然是中阶军将的最下等吧,那也是中阶军将,老秦家还没有过这么般官阶的军将呢,可算是光宗耀祖了,结果,飞了。
“确是可惜了,唉,三郎你鲁莽了,”
秦庆用剩余的左手猛拍大腿,在秦庆简单的想法里,有个武职怎么了,虽然武职让文臣看不起,但是能光耀家门就是了,家中就是赤佬,拨个武职也不寒酸,相反,倒是一种极大的荣耀了。
秦延只是笑着让父兄感慨着,指责着,和他们是说不清这里面的道理的,武职,呵呵,让其他文臣有个居高临下轻视吗,绝不可能,他们那些书呆子也配。
李舜举看着这架砲车很轻松的被拖上了罗兀城的夯土城墙,然后发出了石弹,轻轻松松的飞跃六七十步,激起几丈高的灰土。
这架只需要区区十余人驱使的砲车改变了他所有的认知,东京汴梁城墙上有几十人驱动的庞大的砲车,石弹射程不过也就是这个距离,但是那是多庞大多笨重一个物件,根本无法随军运动,而这个砲车虽然也很庞大,但是分拆后勉强可以随步军行军。
李舜举不能不对秦延感叹,这是什么样的头脑才能想得出来的改变,果然是官家惦念的天才。
李舜举下城后立即派出八百里急报入京,而他自己没有多停留,立即折返米脂,那里有一个能改变这个困局的人。
垂拱殿里,赵頊一脸的阴沉,王珪、蔡确、章惇、孙固、安焘等人静立无言,君王一怒流血千里,虽然有些夸张了,但是赵頊瘦弱的身躯里隐藏着急爆的性子却是真的,谁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来触怒这位帝王。
赵頊冷笑着拍打着桌上的折子冷笑道,
“一个十七岁的白身西军子,一个看到其父被羞辱殴打愤而还击的孝子,竟然引起了刘挚为首的台院的弹劾,而朝中颇有人响应,哼哼,”
赵頊一拍桌案,蓦地站起怒视众人,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有军法不可立军,以下克上者罪之,哼哼,难道要朕的治下百姓忘却孝道不成,如治下百姓看到父母被凌辱忍耻偷生,是不是朕就可以抚掌大笑,大宋大治可期矣,”
赵頊愤怒的吼声回荡在不算大的垂拱殿里。
赵頊愤怒的是,有些人无事生非无风起浪,而且是很没有眼色。
秦延此人从目前种种颇有些文武双全的意味,将来进京谢恩的时候,如有可能他还想陛见的,他要好好看看这个十七岁的西军才俊,如可,将来他是要大用的。
但是现下秦延还没入京谢恩就职就被朝中一些官员贬损至此,这将打击了秦延的名声,即使将来对秦延的官声也有影响,这是赵頊既不愿意看到的,只要是人才赵頊就希望他走的顺利些,最后能走到可以大用的时候,但是秦延还未入仕就被人攻伐至斯,赵頊愤怒非常。
王珪闭目养神,他严格的遵守牌位的定位,他之所以能担任左相,那是因为官家希望缓解和守旧派的矛盾,安抚朝野这些大臣。
当然作为帝王随时都要想着制衡,官家也不希望政事堂只有一个声音,他的作用就是制衡右相蔡确以及章惇等熙宁维新派。
说白了他就是一个牌位,所以很多大事王珪都是不掺言的。
今日左司谏王岩叟为何领着御史台的人弹劾这个小小的秦延,那是因为想通过弹劾秦延来贬损种谔的所谓战功,种谔此人和章惇等人走的较近,都是主战派,深为守旧派主和派的愤恨。
而礼部郎中刘挚等人发难也是因为他们同属守旧派,一起发声声援罢了。
说白了还是逃脱不来熙宁维新派和守旧派的相互攻讦,除此毫不稀奇。
虽然王珪也是守旧派一员,不过他谨守明哲保身,绝不会说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