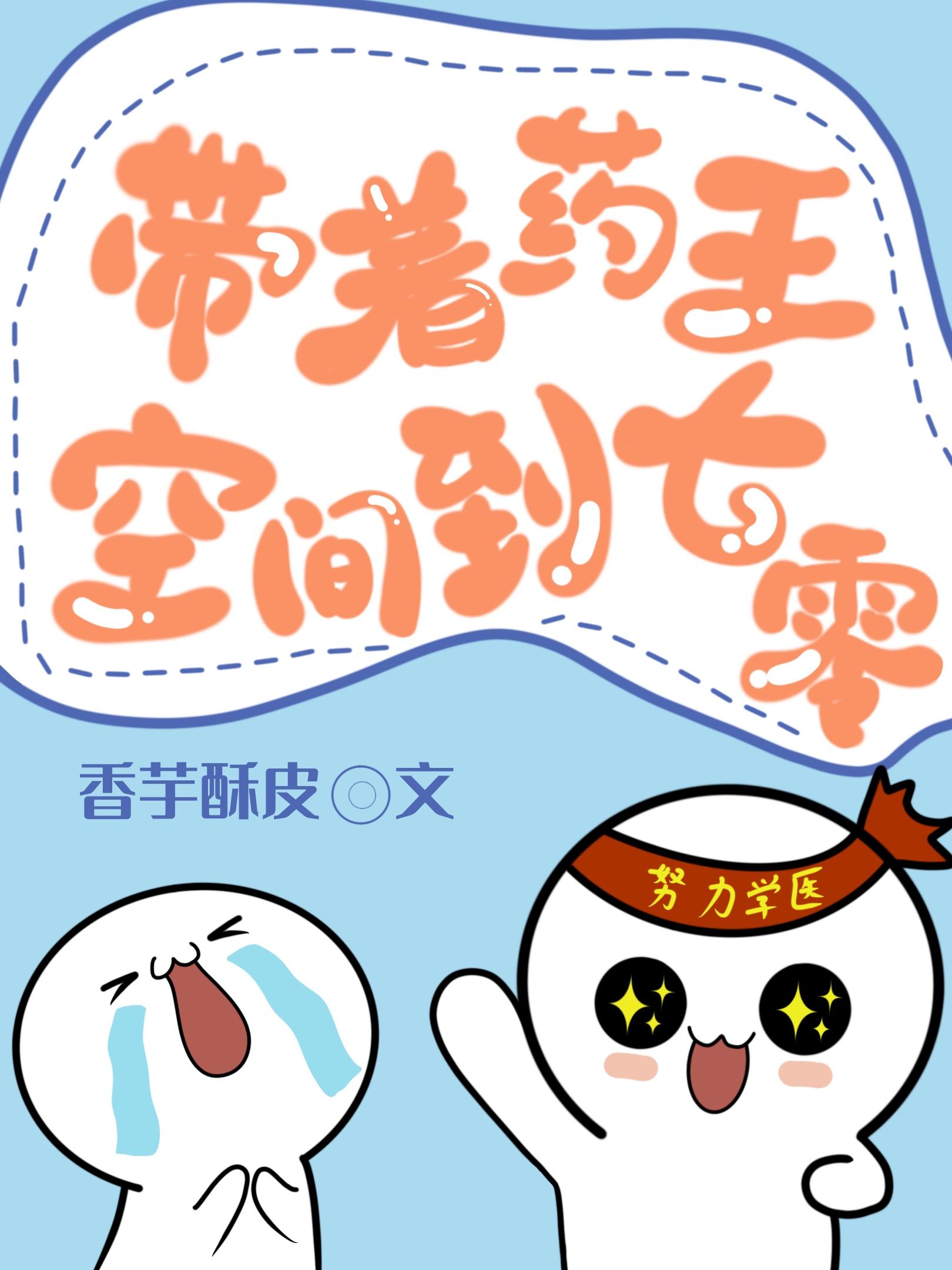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臣相怀了我的龙种全文免费 > 第74章 第 74 章(第1页)
第74章 第 74 章(第1页)
管家瞠目结舌“相国您连这都忘了”
萧让欣然点头,表情忧郁“要不然怎么会说自己记性越发不好了到底也快三十了的人了。”
管家里里外外仔仔细细地辨认了一遍,确定面前坐着的是货真价实的云相,才提醒道“那东西都是您兄长贪污的。”
萧让喝茶的动作顿了顿,万万没想到真相是这样,刚要若无其事地继续问,管家又道“这些年您让老奴想法子暗中还回国库了不少,但因为数目过大”
萧让倏然搁下茶盏,打断“你是说一开始不止四百万两”
管家一脸茫然“是啊,一开始不是九百万两么,相国你连这都忘了”
萧让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又淡然地抿了口茶,模棱两可道“还记着些,只是时隔日久,记忆有些模糊了,你倒是同我说说。”
管家应下,滔滔不绝,显然他先前都是在谦虚,明明记忆好得很。
萧让越听越觉得自己是个畜生。
云歇的兄长贪了近千万两,云歇在之后的十余年里暗中想方设法还着,已经还了一大半,没法还的就赈济灾民了,自己抄家抄到的就是还没处理掉的那部分,他却以为是云歇贪污的。
萧让悔得肠子都青了,努力维系面上的镇定,又问“那上万亩田也是本相的好兄长私吞收买的”
管家越发觉得奇怪,却还是如实道“并非,早年大旱,田地上颗粒无收,您不是一掷千金用良田的价去收购了那些劣质田么”
管家说到这个突然怒填胸臆,义愤填膺“那些个百姓真不是个东西,您好心救济他们,怕他们没粮食饿死才收购他们的烂田,结果饥荒过去了,他们却闹着说您趁乱发财私吞田地、居心不轨,他们这摆明了是想要回自己的田”
萧让嘴里一阵发苦,他之前误会云歇,自己干了那么多恶劣的事,他的相父是怎么原谅他的
要不是有管家在,萧让真想默默捂脸。
萧让记得这事儿当年还闹的沸沸扬扬,强撑着又问“那本相当初为何不解释”
“您解释了,您这也忘了”管家萧让的眼神越发诡异,“您当初气不过,拿出田契了,上面白字黑字都写的好好的,那些个百姓的手印也按在上面,可他们又非要说您是伪造的,外头那些个百姓哪听这些,他们只听他们想听的,哪怕田契上写得好好的,他们还不是睁眼瞎。”
“后来京兆尹出面,抓了不少农民去官府,都已经再三公布田契是真的了,可外头沸沸扬扬传的还不是京兆尹胆小怕事,惧于您淫威迫不得已歪曲事实”
管家越说越气滔滔不绝。
萧让算是听明白了,干涩道“所以本相之后遇上什么事了才都不愿解释”
他这话问的太过反常,无奈管家在气头上,直接忽视了这点,“这事儿当初结了,您就嗤笑着跟我说,您的冤屈没法伸张,因为怎么,您都更符合施暴者的角色,解释有屁用,没人会信。”
萧让心口一阵阵的钝痛。
他总是怪云歇什么话都往心里搁,可站在他的立场上想一想,他是奸臣之后,又权势滔天,人都倾向于同情弱者,没人会信他的委屈。
他就算解释了,也多半是徒劳无功。
萧让只到了云歇什么苦都喜欢打碎了往肚子里吞的性子,却从未想过追求他这性子的由来。
他连责怪埋怨的资格都没有。
更何况云歇幼时备受欺凌,一再回避隐瞒自己的情感,不过是自我保护。
在他的相父那里,袒露喜欢等于给予被伤害的权利。
他的相父明明已经下定决心将自己伪装的无懈可击,却还是给了他宠溺无度的柔软。
那些商铺、那些宝物其中也定有隐情,萧让却不想知道了。
管家目瞪口呆地着云相火急火燎地走了。
第二日傍晚,云歇正在房里打点府上杂事,听见萧让在外边敲门,眼都没抬“进来。”
跟在萧让身后进来的是三四个仆役,手中抬着面屏风样的东西,边上还有两个丫鬟拿着两个竹签叉着的小人。
云歇诧异“这是什么”
萧让吩咐着人把东西放好,给承禄使了个眼色,承禄会意地去将门关好。
云歇就要过来,萧让径自过去,将人按着坐下“相父稍安勿躁。”
说着自己又走到像屏风的那东西后面。
白色的幕布上很快出现了两个小人的阴影,云歇愣了下,失笑,狗东西竟然无聊到倒腾皮影戏了。
萧让清了清嗓子开始演“小皇帝将相父抱到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