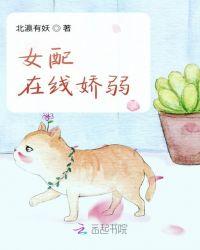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人人都爱马文才梁祝结局 > 第51章 生死危机(第2页)
第51章 生死危机(第2页)
“我实在是不明白在西馆里兴风作浪的那几个士人,宁愿被人偷、被人抢也要在西馆留下,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玩弄我们这些卑贱之人有意思吗若不是放了那些金银财物在面前诱惑鲁仁他们,他们又怎会生出恶意这么多年,他可拿过我们一样东西”
“在我们来是财宝的那些东西,在他们来只不过是常物,所以才没有刻意回避啊。”刘有助想起那些废纸,叹了口气,“自己眼皮子浅又起了贪念,不能怪祝公子他们。他们都是好人。”
“,你又这样了马文才当众斥责你、抢走你东西的耻辱你已经忘了祝英台若是真得起你,第一次为什么不给你那些练字的纸你我为何丢了吏算吏的差事,你都忘了对他们来说都不算什么的那些,却是你我费尽千辛万苦流尽了血汗也得不到的”
伏安激动地胸前起伏不已。
“你忘了,我没忘”
他们都在忘,他们如今都只得到那几人,他们都已经忘了士族只是花团景簇下隐藏着的毒蛇
“有些事,必须得忘了,不忘了怎么继续往下走我们虽没得第一,但这么多年的努力难道就白费了吗这些所学之得才是真真切切归我们所有的东西。”
刘有助见伏安已经有些魔怔,不忍心这个性子本来就暴躁的朋友钻牛角尖,好心开解着。
“你算学好,我现在也可以去抄那面墙练字了,他日只要找到愿意留用我们的主官”
“哪里有愿意留用我们的主官我们这群没后台没钱财的穷生,谁愿意用我们”
伏安冷笑着,突然转过脸,又盯着刘有助。
“你自那天回来后就态度大变,你又不肯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你到底是怎么挨的杖子谁要打你”
刘有助身子一僵。
“我说了,我,我确实做错了事,这事不能说”
“是不能说还是不敢说你是被人威胁了对不对”伏安面色更冷,“你不说我也知道,你那晚去甲舍了,我那晚见你被马文才提去馆主那了祝英台为什么第二天要写那面墙是不是对你心中有愧”
刘有助一惊。
“你晚上又去”
伏安没接他的话,当是默认。
“你不愿意多说就不说,我你恐怕不是冲撞了祝英台,就是冲撞了马文才,也许两个都冲撞了,这是在杀鸡儆猴呢”
伏安哼道“祝英台起来温和,骨子里还是个士人,他们是被他温和的假象骗了,忘了他的身份,等再遇见这种事情,他还是会把你我这般位卑言轻之人推出去。”
“你不要胡思乱想自从朱县令拒绝了我们的差事,你就越来越偏激了。”刘有助心里很是难过,“这世上总还有好的主官的,像是祝英台那样的士族,当了官也会是好官。”
“指望别人有什么用。”
伏安木着脸说“指望别人能对自己好,才是真的万劫不复。”
一时间,屋子里只有刘有助细细的呼吸声,气氛越发的凝滞。
就在此时,屋子外面突然传出了刺耳的犬吠声,那犬吠声又急又快,听得人心烦气躁,伏安本就满腔怒火,听了这犬吠声后一声大叫。
“谁在丙舍里养的狗不知道病人需要静养么”
边说,边抬腿跨了出去,准备将门外的狗赶走。
谁料他一出门,抬眼便和马文才、傅歧等人打了个照面,身子不由得一僵。
“这里还住着人呢”傅歧好奇地着明显是杂物间的屋舍,“我还以为是空置不用的杂房。”
马文才则是蹲下身安抚着自己的猎犬,抬头问眼前面色难的伏安“你住这里”
丙科都是大通铺,一屋子里住七八个人的有,住十个的都有,这杂物间再小,也有大半个甲舍大,起来不像是伏安住的地方。
“我不住这里,刘有助在这里养伤。”
伏安强逼着自己若无其事,皱着眉头着面前诸人“你们几个公子哥,跑来这里干什么”
“难道是刘有助不是说受了杖下不了榻么何况早上也没来”
傅歧心急口快地问了出来。
他们是特意来的
伏安的后背顿时惊出了一背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