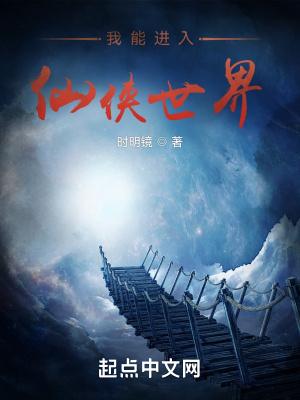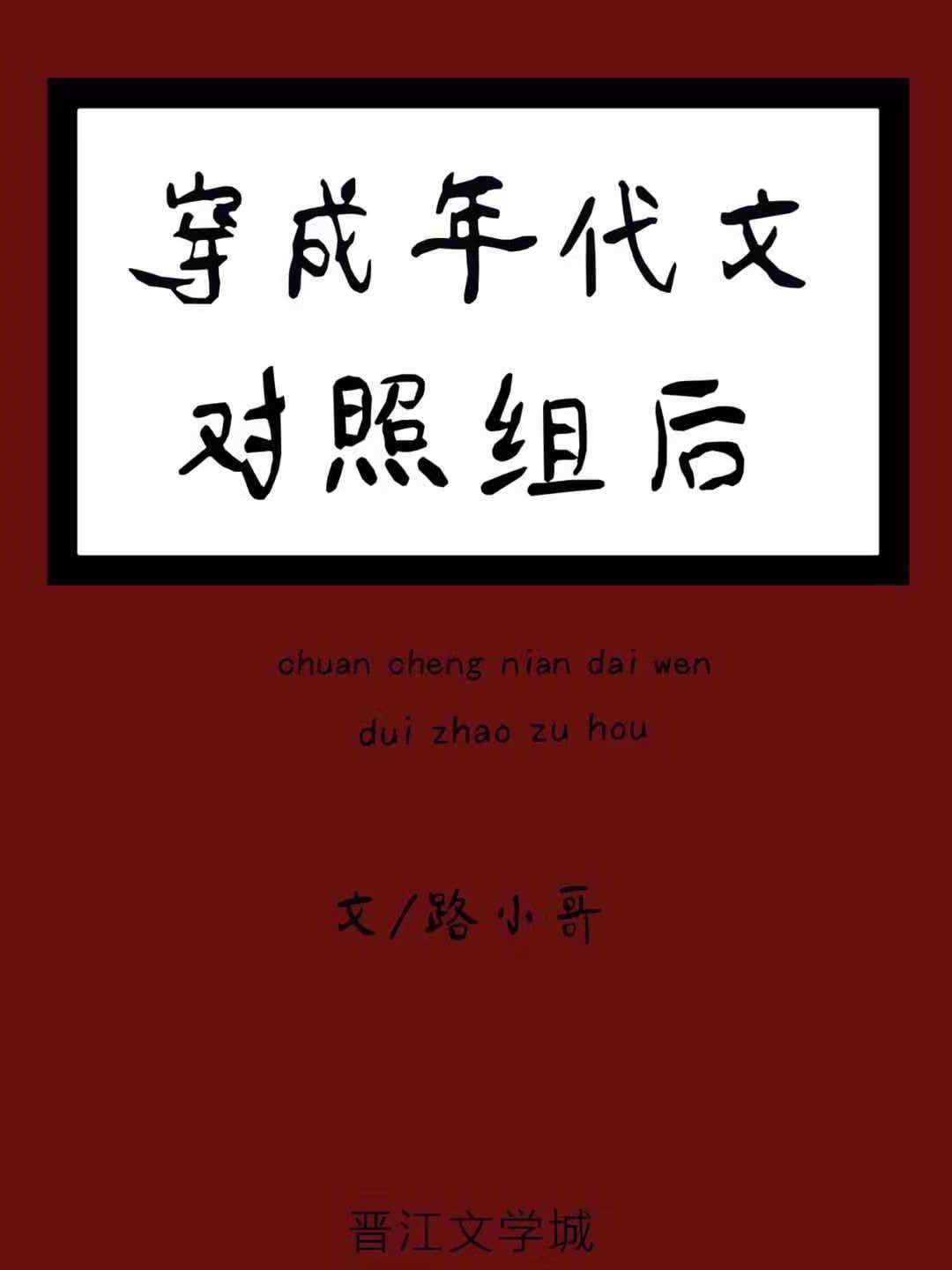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人人都爱马文才梁祝结局 > 第154章 鹰扬虎视(第1页)
第154章 鹰扬虎视(第1页)
“马兄,外面那是”
站在窗后的梁山伯面露担心的向马文才,外面那人的气势太盛,即便隔着门窗,他也能感受到那种久居上位的高傲和自信,更因为他话语中对祝英台的熟稔而感到惊讶。
然而比他更惊讶的是此时此刻的马文才。
同样站在窗后的马文才却不能像梁山伯那样带着好奇去打探,他整了整自己因为受伤而穿着的家常衣衫,表情有些复杂地叹了口气。
“那是祝英台的兄长,祝家庄的少主,祝英楼。”
“兄长”
梁山伯还没来得及表现出自己的诧异,马文才已经推开门,出了屋。
见“衣衫不整”的马文才出了屋,那俊逸的青年先是皱着眉露出不赞同的表情,大概是觉得他出来的速度太慢了,不悦的表情更甚。
“你就是马文才畏畏缩缩,伸头探脑,果然鬼祟之辈”
听到他的评价,马文才身边的疾风、细雨齐齐露出怒色,这祝英台的处事阅历是个有眼睛的都得见,若不是他们家公子把他护的滴水不漏,早在河里就已经淹死了,更何况从马文才成人起,谁见了他不夸一句“兰芝玉树”之材,结果到了这位祝家少主口中,就成了猥琐鬼祟之人
两人忠心护主,一时怒视着祝英楼,大有马文才一旦开撕,立刻力争到底的态度。
可一向高傲的马文才却没有动怒,甚至连气愤的神色都没表现出来,反倒坦然地点了点头。
“是,我便是马文才。”
“好,好一个你就是马文才”祝英楼见他坦然认了,倒比他之前在屋中不出冷意更甚,“你既然知道祝英台的身份性格,居然唆使她离开学馆,更是几度将她陷于危险之中,你是当我祝家庄无人了吗”
马文才带祝英台离开时,不是没想过祝家人会生气,但那时他心中已经肯定祝家对这门亲事有了默契,估摸着祝家人即便生气也不会到震怒的地步。
何况他将祝英台当做了“自己人”,比起祝家庄的感受,自然更顾及祝英台的感受,他有意交好祝家,便以她的意愿为了先。
这件事上,要祝英台是男人,祝家庄还要谢谢他照顾同窗之情,自是一点错都没有的。
可祝英台是个女人,马家还曾为了两家子女议亲,到了“同窗共室”的地步,只是没最后过了明路,而马文才明知祝英台是个女人还拐她抛头露面一路同行,只要有点城府的人,都会觉得马文才有些卑鄙。
马文才也是有苦说不出,这一路明里暗里都有人保护,他原本估计着绝不会有什么危险,哪里知道一路上危险重重,好几次甚至有性命之忧,这原本只是一场“游玩历练”的辩驳理由显得太过虚弱,使得向来善言的他竟说不出话,只能低着头又认了。
“这一路颇遇不顺,此事是我太过大意我有不可推卸之责。”
莫说疾风、细雨,就连刚刚跟着出来动静的梁山伯都大惊失色。他们见过各种姿态的马文才,就连向徐之敬求助救人的时候都是以公平交易的姿态求人,何曾有过这样低三下四、委曲求全的时候
一时间,梁山伯似乎隐约明白了点什么,心中莫名一酸,像是被什么刺了一刺,他虽极力将那种酸刺压下,心中的那份了悟却越发让他感到酸涩。
他定了定神,强迫自己向祝英楼的形容相貌,而不是老注意着马文才和祝英楼的对峙。
这一,梁山伯更加心惊。
祝英楼和长相秀气的祝英台面貌绝不相同,只有从不同于常人高挺的鼻梁中能找到两人血脉相连的一点联系。
祝英台相貌阴柔中带着沉静,而祝英楼却是“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加之鼻梁高挺,整个人显得说不出的鹰扬虎视,若论长相,马文才年纪尚轻,可他长相正是南朝审美中最具有认同感的那种清朗,可要以梁山伯评判,与人交往,祝英楼这种长相气质的男人才最让人心折。
是的,男人。
与祝英楼相比,即使在梁山伯来如此优秀的马文才,也显得太稚嫩了点。
在兴师问罪的祝英楼面前,马文才的谦逊倒像是做错了事的小孩在接受着家中的质问一般。
不仅仅是梁山伯一个人这么认为,那眉头紧蹙的疾风、细雨,还有跪在地上仰着脸满脸担心的半夏,在祝英楼惊人的“强势”面前,都已经表现出了这种不安感。
显然祝英楼没有祝英台那么好说话,这位盛气凌人的青年听到马文才光棍的全认了,一双眼睛露出凌厉的光芒,怒喝道
“什么叫颇遇不顺我截了你那家人送出去的信,这一路岂止是不顺若我没有找来,你是想让英台餐风露宿这么回去不成还有你如今这样子,明知我上门问罪,竟如此孟浪的出来迎接”
他着马文才甚至未曾严密掩上的衣襟,不满之色更甚,伸手在腰间一抚,那镶金嵌银的细长腰带立刻变成了一根软鞭,带着赫然的风声向着马文才肩头挥去。
“真当我祝家无人,急着高攀你这太守之子了是吧”
这一鞭来势汹汹,势头却不疾,以马文才的身手,微微退避就可以躲开,可马文才听到耳边风声赫赫,不避不让,竟硬生生吃了这一鞭子。
祝英楼原本就是江东诸多庄园之中名声鹊起的青年才俊,早在四五年前就已经负责祝家庄甲兵的日常操练、武备,手上功夫不弱,尤其是一手鞭法,家中犯事的奴仆庄户之流无不闻之变色,更何况马文才原本就有伤在身。
这一鞭子下去,马文才原本才养好的伤口顿时重新皮开肉绽,鲜血飞溅而出,染红了整个衣襟。
“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