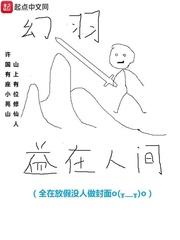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p盲d盲w > 第19章(第2页)
第19章(第2页)
她坐在我的对面,眼里也已经没有了那张证件照上的懦弱,反而在锐利之下透露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兴奋。
许锐没有脱下帽子,反而拽低了些,她遮住自己的眼睛,缓缓开口:“未来的警察小姐,你找到我了。”
没有昨日下午在河边的尖叫,没有愤怒的不语,没有那日激动的冷嘲热讽。
许锐露出了和北川如出一辙的神秘笑容:“这下你查到哪里了?贝成山与明辉的关系?潇潇的死因?还是说,你只是用私权,查了我的档案?”
我深呼吸一口气,没有理会她的挑拨。
见我久不说话,她皱起眉来,拿起书包作势要走。
我淡淡抬眼看她,故作轻松地朝椅背上靠去,平稳地端起桌面上的咖啡杯,丝毫没有想要挽留的姿态反而引起了许锐的注意。
她果真将手又从书包上放了下来,转身面对我:“你想说什么?”
“许锐,我虽然只是一个学生,但是你也不要小瞧了警校的人。”我透过她的眼镜框强行与她对视,“我能查到被记录下来的真实,尽管你们有时候并不认可这种真实,但它却又是必须存在的。”
“哪怕这样的真实不是真实?”许锐笑起来。
“不,对于我们而言,记录下的一定是真实。作为观众,每个人的角度都是不同的,一个事实自然不能从一个人的角度去解答。我明白你对这样的事实抱有怀疑并不屑一顾,但你若想更改既定的事实,必须拿出足以推翻它的证据。”我放下咖啡杯。
“就像,”我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纸,面朝着许锐的方向打开,“你们想让我证明张潇然的死不在1月8日,就得拿出12月时,她受伤的证据。”
纸条上写着的,是一个日期——
2005年12月13日。
这天,是汪时瑞住院的日期,我昨日回复完汪时瑞短信后回到了公安局,借口想要学习如何写档案记录,科员大姐见我没再把注意力放在居民个人信息上便放松了警惕。
我从2006年1月往前逐日翻看,终于在2005年12月20日的一次记录中,找到了汪时瑞的父亲报警称汪时瑞受到严重故意伤害的记录。
记录中写道,汪时瑞于12月13日晚23点左右住院观察。
由此,我才敢大胆地推测,张潇然的死亡日期,恐怕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附近。
许锐的表情在看到我的纸条时一下变得僵硬起来,她的身体开始剧烈地颤抖,好像是回忆起了恐怖的过往,我有些担心强烈的刺激会使她受不了,于是立刻收起了纸条。
她见视野中的障碍被清除,立刻抓住了我的前臂,红血丝不知何时已经布满了她的眼眶:“你还查到了什么?”
我被她的突然袭击吓了一跳,我注意到,她的那双眼睛里充斥着的并不是名为恐惧的东西,而是一种极度的兴奋,好像是亲眼看到了某部大型连续剧的结局,她克制地压着上扬的嘴角,再次问了我一遍:“你还想到了什么?”
我本想将我的推测作为我进一步沟通的王牌保留下去,却在此时被她这般令人胆战的目光引出了口:
“贝成山与明辉,曾经有不正当关系。”
2008年·入局
许锐听完我的猜测,冷哼了一声,便靠在椅背上盯着我看。